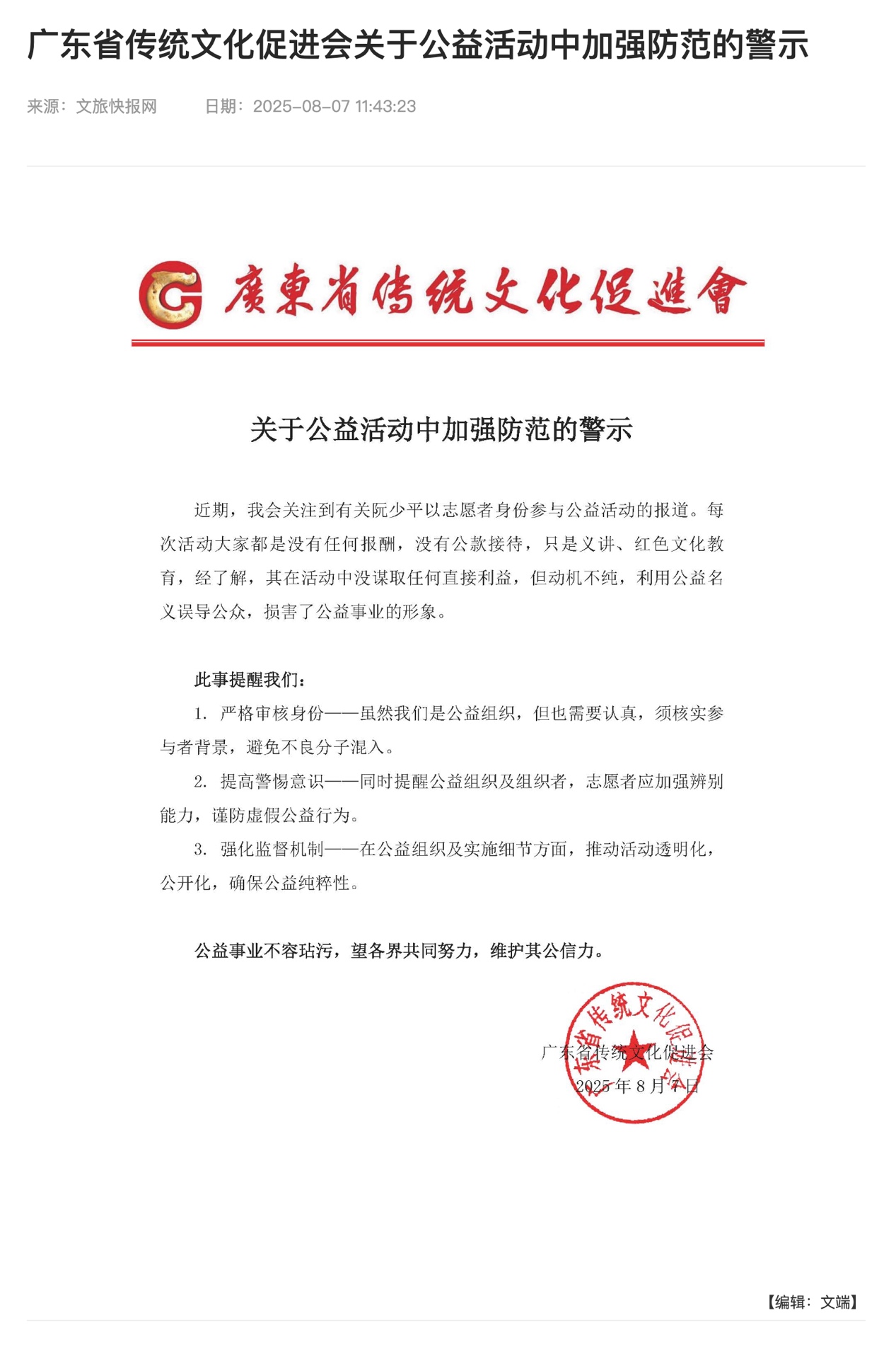在“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初高衔接”之后,“高大衔接”也横空出世。
在北京海淀区某大厦一间挤满学生和家长的教室里,海报上“大一新生暑期蓄力,入学抢跑一步”的标语,无声地宣告着另一场发令枪的提前鸣响。一位刚参加完高考的女生无奈地说,从小学就开始上这家机构的课,没想到大学也要来上。

2025年7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国际财经中心。在一家教培机构的大学衔接班试听课上,来听课的除了准大学生,还有不少学生家长。(南方周末记者杜寒三/图)
“高大衔接班”现象本质上是教育“抢跑文化”在大学阶段的延续。在“高大衔接班”的课堂里,有高考英语147分的孩子在学英语六级;也有家长认为“现在给孩子灌输一些知识,总比不灌要好,没有坏处”,孩子被“软硬兼施”送过来的。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高校也加入了这场“衔接产业”的盛宴,纷纷推出收费不菲的衔接课程。这些课程虽然被冠以知识填补的名目,实则暗含了高校在非学历教育创收驱动下的利益考量。教育机构与高校共同将“衔接”打造成一门炙手可热的生意,家长的焦虑被不断催化放大,让这些已满18岁的年轻人依旧无法喘息。
高考后的暑假,本应当是青少年告别高强度应试训练,迎接自主探索的宝贵“心理过渡期”。然而衔接班课程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9点,25天填鸭式“大学预备营”甚至高达一万多元的天价夏令营兜售的所谓“有效社交”与“目标感”,都在粗暴地剥夺成长的空隙。在长期被外力填满的日程中,孩子们的自我规划能力与内在动机的发育会受到阻碍,原因很简单,所有方向都由外界预设,“自我”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曾经,在复旦大学迎新大会上,朱大潜院士曾郑重指出,从中学到大学,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学习要求和学习环境都有重大的变化,建议大家认真体验、讨论与总结,将自觉地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作为开始阶段的第一要务。“自觉”二字正是大学教育区别于过往教育的本质所在。
18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在神经科学层面,前额叶皮质的发育也已基本完成,赋予他们理性决策与承担责任的生理基础。所谓“衔接”,核心应是学习方式的转变,而非只是内容的提前填塞。而类似于“保研陪跑班”这类38个月全程保姆式服务,表面是助力,实则是对学生自主能力培养的慢性扼杀——当学习计划需要“详细到以周为单位”由他人制定,论文署名靠机构“合作导师”挂名,竞赛奖项在“纯保姆式”协助下获取,独立人格的成长空间又在哪里?

在古希腊,青年通过成人仪式独自守护城邦边界来确认成年身份;在非洲的一些部落,少年需要独自完成荒野生存挑战才能被接纳为共同体成员。这些古老仪式的核心精神,在于通过赋予责任与信任来确认成年的资格。今天,站在大学门槛前的18岁青年,所要面临的真正“衔接”并非提前修读高数或者英语四六级,而是家长敢于放手、社会给予空间,让他们在试错与探索中完成向成人的心理过渡。当父母们担心“别人孩子学得这么有系统性,已经赢在起跑线上”时,他们或许不明白,人生的赛道已经悄然改变,真正的起跑其实在那些被允许自主决定方向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