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足山在富有众多壮丽和秀美山川的西南地区,并不以自然景色见长。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也默默无闻。直到明清之际,鸡足山一跃成为迦叶道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共尊之。此外,在本地政治精英的书写中,鸡足山还和大理地方的政治历史记忆、道教洞天福地思想相结合,从而与汉、白、藏、傣各族人民发生紧密关联,并且成为构建大理当地社会生活不可缺失的要素。如何理解一座自然山川汇聚了如此多元符合的文化?《“共见之处”:大理鸡足山的多重世界》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尝试揭开鸡足山一层又一层厚重的文化面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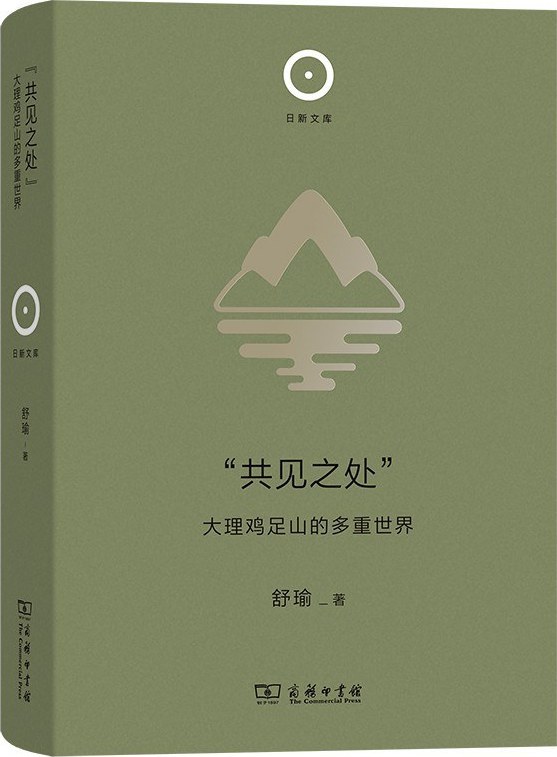
《“共见之处”:大理鸡足山的多重世界》,舒瑜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8月出版
齐群:我们一谈到大理,首先想到的是苍山洱海、风花雪月,却很少关注鸡足山。您研究大理为什么会选择鸡足山?
舒瑜:苍洱之间的大理坝子是大理的腹心地带,而鸡足山位于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位置在洱海东岸。从今天的挖色、海东这一带是有山路直接可以达到鸡足山的。在1943年,费孝通、潘光旦一行到鸡足山朝山,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他们是先横渡洱海,然后从挖色骑马上山的。鸡足山顶峰有著名的“绝顶四观”,其中有“西观洱海”一景,在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鸡足山的顶峰看到洱海的一角。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并不是太远,现在高速公路修通之后只要一个小时左右车程。
相对于苍洱之间的大理腹心地带来说,鸡足山是一个边缘地带。但是鸡足山在佛教世界的名气非常大,鸡足山被称作是“光明世界”“迦叶道场”,它是佛陀大弟子迦叶尊者守衣待弥勒出世的佛教圣地。所以今天鸡足山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众共尊的佛教名山。
我之所以选择研究鸡足山,是有历史人类学角度的考虑的。苍洱之间的大理是一个“坝子”,这里我先说一下什么叫“坝子”:它是云贵高原一种非常普遍的地貌,指山间比较大块的平地。大理“坝子”的北边有“龙首关”,南边有“龙尾关”,即今天的“上关”和“下关”,在两关之间的百二山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从南诏国到大理国,大概是从公元738年到1254年,持续了500多年时间,差不多是和唐、宋两个中央王朝相始终的一个地方政权。
《“共见之处”》写作的时间起点,是公元1254年蒙古军队平定大理、大理政权覆灭。我关注的议题是大理地区在元明以来的社会历史转型,也就是大理从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的中心转变为中原王朝治下的西南边陲的过程。鸡足山的兴起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明初时大理这个地方出现一本书叫《白古通记》,这本书被侯冲老师称之为“白族心史”。他认为这本书是大理的地方精英基于“夷夏之辨”而做的心史创作。它的写作背景,就是明初朝廷对大理本地文化进行毁灭性涤荡之后,大理的地方精英分子重新书写他们的历史,试图说明大理在明代以前并不是一个声教未开的蛮夷之地,而是一个佛法兴盛的“妙香国”。所以在这本书的书写中,大理地区的重要山川景观就被“佛教化”了。比如,苍山被说成是“灵鹫山”,是释迦讲法华经的地方,苍洱之间是“妙香城”,“鸡足山”这个地名也是在这本书里出现的。有很多学者考证,鸡足山本来位于印度,是在明代这个地名从印度被移植到了大理。这本书还写到,迦叶尊者从苍山入鸡足山。在海东双廊的青山村这个地方,现在还有迦叶尊者足迹的遗迹,还建有一个圣踪寺。
我在田野调查中听到很多从苍山到鸡足山的叙事,比如,迦叶尊者是从苍山入鸡足山,然后为鸡足山选址的这只金鸡也是从苍山飞到鸡足山。还有我的书中第二章重点讨论的“云遗石”的传说,这块补天的仙石从苍山落到了鸡足山。我感觉从苍山到鸡足山的叙事线索,更像是心态史的表达,它要表达一种转移,同时转移当中又是带有连续性的。所以从苍山到鸡足山的空间线索,也是我这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述脉络。鸡足山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我们理解大理在元明以后的社会历史转型的关键点。此外,我也想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大理,那就是山川研究,所以我选择了鸡足山。

云南大理,鸡足山佛塔
齐群:西南地区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转型,元明之际是很重要节点。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大理本地的政治精英有一系列的努力,其中一项是撰写山志。书中讲鸡足山的崛起——鸡足山原名“九曲山”,“鸡足山”是在本地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不断构建中,把佛教的地理观借用过来,从此九曲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而这个过程不只是本地人的推动,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在大理地区的发展,也对这个地方成为佛教圣地有助推作用。如果说禅宗是佛教中国本土化之后的知识形态,方志书写是中国经史传统的知识形态;那么二者在鸡足山的展现,都是知识形态上的迁移。您怎么理解政治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直接改变和知识形态传播渗透地方社会这二者的差异?以及不同的知识形态在鸡足山的发展和崛起过程中扮演怎样的作用?
舒瑜:我在研究和书写过程中,是把苍山和鸡足山来做一个互相参照的分析,二者互为镜鉴。从元朝到明朝,大理发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历史转型,尽管同样都是进入到大一统王朝内部,元代时大理还是有一些特殊性,朝廷设置了由段氏世袭的大理总管,所以大理段氏还是有一定势力。但是到了明代,这个情形就完全改变了,明廷以非常系统的方法——先是武力征服,之后开始定租赋、筑城隍、兴学校、立卫堡、广屯田、创建诸司衙门,用这一系列措施把大理纳入中央朝廷统治之下。大理也是西南地区第一个设立府治的地方,在洪武十五年就设立了大理府,朝廷开始派驻流官来治理大理。
所以我在书里第二章就提到大理“内域化”的过程就体现在苍洱之间大理坝子的这个空间内。这个过程里,我觉得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是苍山神祠性质的变化。赵丙祥老师有专门的文章写南诏册封“五岳四渎”的事情。在这样一个“仿中原”的岳渎体系中,苍山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五岳当中的中岳,同时也是南诏和唐朝会盟的圣地。但是到了明代,大理本地人再把苍山当作“中岳”来祭祀,就成为僭越之举。所以我看文献记载,到了明代中期,苍山神祠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改造,把它从祭祀南诏的中岳转变为祭祀地方的苍山神,而且整个祭祀礼仪是完全按照儒家的仪轨规范了请神、迎神、送神的程序,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巨大转变。同时,苍山也开始建设各种书院,其中有一些书院是在毁佛寺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大理府志》的记载里,大理府的祭祀系统不断和中原趋同,和中原省份的州县一样,设立了社稷坛、城隍庙、文昌祠、八蜡庙等,这就是我所说的“内域化”的过程。
明代云南的治理模式仍是二元的,有一种说法叫“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三江之内宜流不宜土”,也就是说,土司治理和流官治理这两套体系是并行的。在苍洱之间大理府的区域中可以看到,国家统治是用儒家的礼制教化来推行的。鸡足山虽然在行政隶属关系上也属于大理府,但是它所在的区域是大理府、鹤庆府、姚安府和北胜州四个府州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是流官的力量难以企及的地方。而鹤庆府、姚安府、北胜州这些地方在明代都是土司治理。明初这里曾经有一次持续了100余年的“铁锁箐夷乱”就是发生在这片山区。在平定夷乱的过程中,明朝特别倚重这些土司的力量,在剿平夷乱之后,土司的势力不断深入到山区,在山区建立佛教寺庙,来提升土司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连瑞枝老师在这方面做了专门的研究。
所以我看到苍洱之间的大理坝子和鸡足山确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治理模式:大理府这边是一套很明显的儒家教化和礼制秩序;而在鸡足山,明廷采取了相对比较柔性的、灵活的,依靠佛教进行治理和教化的路径,形成儒家之外“儒释相翼并行”的教化传统。明廷也非常支持本地土司护持佛教的实践,通过敕建寺院、任命僧官等一系列措施,鼓励这个地方通过佛教导化边民。在我看来,这种政治实践有非常明显的多样性。
谈到知识类型的问题,特别是佛教禅宗,为什么它可以成为最后的推手,把鸡足山从元朝之前一座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塑造成明代中后期的佛教名山?实际上,大理地区从南诏国后期到整个大理国时期,都是佛教非常兴盛的地方,按照古正美老师的研究,她认为南诏和大理国是利用佛教意识形态治国的一个典范。佛教是大理国的国教,上至帝王、世家大姓,还有它的教养阶层、知识分子都是信仰密宗佛教的,也就是陈垣先生所说的滇南的佛教一开始是从西边传入的密教,后面才是从东边传入的禅宗和其他宗派。在这个过程中,教养阶层(就是所说的知识阶层)的转变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大理国期间,科举选拔有一科科目叫“佛举”,通过的人获得“释儒”的身份,这部分人既能读儒家经典,同时又通佛经,这批人是大理国官吏的备选阶层,也就是说大理的知识分子和官吏都是从这个阶层出现的。
大理段氏政权覆灭后,释儒也发生了转型。在元代时,郭松年的《大理行记》中就写到了“师僧”这个群体,释儒到了元代已经变成教童子读书的师僧的角色。在明代,师僧仍然存在,但本地官吏已经不再从这些人中选拔产生,朝廷的科举是官员选拔的唯一方式。所以在这时,大理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完全转向了儒家教育和科举选拔,由此产生本地政治精英。这些人信仰的选择自然也受到了当时本地兴盛起来的禅宗佛教的影响,其中特别著名的是李元阳,他是大理本地的名人,嘉靖年间的进士,官至翰林,他成为明代特别重要的“禅悦之士夫”的典型代表,他曾经在鸡足山修过宾苍阁,在此读书,和僧人广泛结交。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本地新兴的士人群体,他们选择了禅宗这种新的知识分子宗教作为他们的主要信仰。所以禅宗能够在大理扎根,能够在这个土壤里很好地生长,一方面是因为大理本身有非常浓厚的佛教信仰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和明代之后本地知识分子群体信仰转型,以及禅宗从东部滇池地区不断往西部大理地区传播,鸡足山由此成为禅宗的重要据点,这样一个知识形态变化和传播的过程,是特别相关的。
所以我认为禅宗是中原的佛教文化和大理本土佛教深厚的根基相嫁接的一个非常好的中介桥梁。
另外,我补充一下。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后来为什么说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力量可以很顺利地进入西南地区?其实佛教已经为它铺平了道路。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以为,好像只有封建状态才能创造多元。在某种意义上,恰恰相反。后来明清朝廷中央力量的进入,才让西南当地更多元了。这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我举个例子,比如在丽江。明末徐霞客到丽江的时候,当时接待他的丽江土司接待他,对他很好,还请徐霞客批改自己的诗文,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很多地方就是不让他进去,比如玉龙雪山。我读一部《丽江县志》,里边怎么说的呢?有一篇碑记说,到了清代初期,本地儒生还在发牢骚,他们说,丽江土司很霸道,一旦发现老百姓家里出了天资聪明的孩子,就想办法打压,不让他读书,大概是怕这些孩子参加科举考出去了,反过来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有些土司其实是对多元有抵制的。直到清代,丽江的文庙还是很小很简陋。丽江土司特别鼓励自己的子弟读书,“天雨流芳”的意思就是“读书去吧”,但又打压本地聪明的平民孩子。丽江后来出了很多很多人才,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发达的文化中心之一,在以前的土司治理模式下是不太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中央朝廷打破掉了西南地区类似于部落社会的格局之后,才促进、推动了多元,如果没有明清中央朝廷的推进,云南、贵州等很多地方反而形成局部或者地域社会的一元化。这是我想做的一点补充。
齐群:在日常生活里,鸡足山和大理地区的人,和宾川县的人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围绕鸡足山做了哪些他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仪式呢?
舒瑜:确实我的这本书相比之前鸡足山的很多既有研究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有一部分关于山下的乡民社会的田野调研。这部分研究在之前的研究中是比较缺乏关注的,因为研究鸡足山的人都只是看到山上的佛教、佛寺的演变过程,以及鸡足山崛起的过程。因为专业背景的原因,我对山下,特别是对山下和山上之间互动关系颇为关注,这部分是很具体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我这里只能大概总结一下总体感受。
我觉得山上和山下是非常复杂的一对关系,他们不一定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鸡足山以“灵山一会坊”的山门为界,山上是完全的素食,而山下乡民社会在山门外有两个庙,这两个庙分别祭祀他们的本主,而且一定要杀生,他们献祭的公鸡一定要到这两个庙外现场宰杀,所以它有血祭的传统。而且当地人认为举办仪式不杀鸡就不灵,因为这样,山下的村落和山上的寺院之间是有摩擦的。
但是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调适。山上寺院派驻山下大庙的僧人就通过劝说,或者现场为这些公鸡皈依,念往生咒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冲突。如果实在劝解不行的话,他们还是会让山下民众按照他们的传统进行仪式。所以两者在长期的相处中有不少摩擦,但同时也在努力地调和。
鸡足山对山下的乡民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在我的研究里我觉得他们的生死都是和这座山相连接的。我在书中谈到比较重要的两个仪式,一个是在鸡足山的神圣景观华首门,也就是迦叶尊者入定待弥勒出世的地方,前面有个太子阁,他们要在这个地方“打太子”来求子;另外一方面是人死之后,大理白族的普遍信仰,认为“人死就是归山了”,如果他们说人死了,会很含蓄地跟你说“这个人上山去了”“他去守山了”,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说法。鸡足山因为是佛教名山,山下人送魂仪式当中,这个魂灵的路线更复杂,人们认为华首门就是进入另外世界的一个入口。所以华首门在乡民社会的生死观里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内容整理自商务印书馆“日新文库”第四辑新书对谈会的部分内容。《“共见之处”:大理鸡足山的多重世界》即是“日新文库”第四辑新书之一种,它通过历史人类学研究,描绘了大理鸡足山的“多重世界”及其联结的途径,生动展现了西南地区多元文化群体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