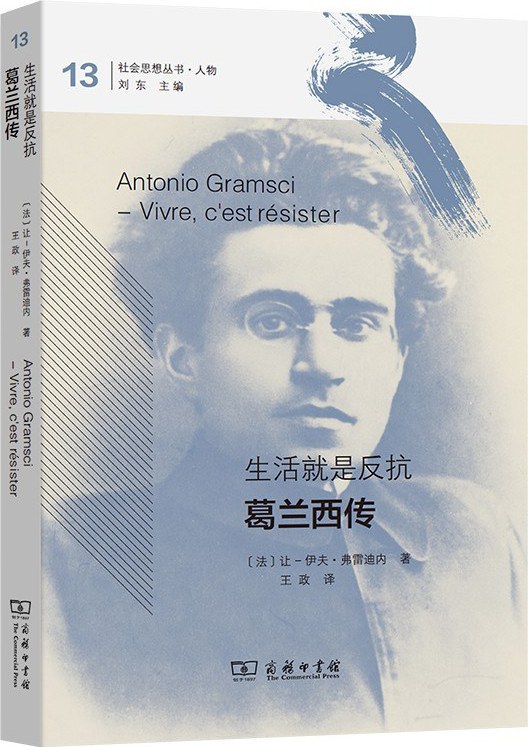从20世纪传承下来的食物系统已经不再奏效。
——奥利维尔·德舒特,《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最终报告:食物权的变革潜力》(2014年)
1945年以后世界的食品系统的发展,通常被视为一段美国化和全球化的历史。不过,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本书前述的那两个世纪的历史。到1945年,英国的营养转型及其全球系统所产生的结构、理念和问题已不可能轻易逆转。随着肉—小麦—糖三位一体和(如今以石油为动力的)“大星球的哲学”成为发展的正统,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强,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信息、资本和商品的流动速度之快,使得人们对饮食的追求和欲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重塑。动量变成了加速度,小问题变成了大危机。在21世纪初,食品系统与相互交织的生态、经济和生物危机密不可分。这场持续的危机几乎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食品系统中多重问题的放大版,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英国的食品系统鼓励消费者从最便宜的地方购买肉类、小麦和糖,并鼓励消费者将这种饮食方式与地位、力量和发展联系起来。以特定食品为生产导向的“第二自然”以及消费者的口味和偏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协同一致的而且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个趋势推动了生物学和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新陈代谢失调、土壤侵蚀、硝酸盐流失、大量化石燃料投入、森林砍伐以及食物供应不平衡等问题。到20世纪后期,古老的英国饮食结构通过无数极具吸引力的烹饪形式,成为世界各地发展的饮食模式。其后果就是这一体系的倾向(disposition)在更大范围和更具破坏性的尺度上发挥作用。最终导致了今天加剧的全球性健康和环境危机—肥胖、营养不良和气候变化交织成的全球症候群,而如今若要减缓和逆转这种势头,已变得极为艰难。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不是在1945年才凭空出现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系统的崩溃
构建一个由全球机构监管的世界食品系统,这个构想产生于 1945年之前。国际农业协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成立于1905年,以整理、统计数据为其主要工作。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涉足全球营养问题,其制定的营养标准成为英国二战期间饮食政策的基础。2 1943年温泉会议(Hot Springs conference)的参会者并非外交官员,而是营养学专家。会议敦促各国采取集体行动提高生产水平,这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农业经济学家约翰·布莱克(John Black)于1943年再次有力地阐述了全球适足膳食(adequate diets)的概念,强调“适足膳食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可以实现的”。实现适足膳食的方法就是建立国际机构来管理食品问题,并促进食品的生产和组织化。
1943年,约翰·博伊德·奥尔(John Boyd Orr)指出,英国将继续位居战后世界食品系统的中心,“因为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市场”,其食品政策必然具有全球影响力。他乐观地认为,英国可以利用其殖民的经验,通过提高产量和减少饮食的不平等,成功地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1945年,奥尔出任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即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的第一任总干事。他设想建立一个全球食品委员会,以真正跨国的方式协调全球食品系统,他特别要求借鉴战时的组织,即1942年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食品委员会(Roosevelt and Churchill’s Combined Food Board)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奥尔提出通过该委员会提供贷款、设备和技术,刺激农业发展,创建和管理粮食储备,并控制全球食品价格。这种受控的经济模式建立在这样的主张之上:“食物是生活的基本必需品,必须与其他非必需品(如汽车)区别对待。”对奥尔来说,粮食委员会是迈向世界政府和全球代谢平等的明确一步。
然而,这个试图超越国家利益的真诚尝试没过多久就失败了。根据奥尔的说法,在1947年4月于华盛顿召开的讨论世界食品委员会设立可能性的会议上,英美双方“都决心压制这一计划”。美国代表团,尤其是国务院,认为此类方案与美国产品寻找自由市场,以及利用粮食援助追求地缘政治目标的优先事项相悖。而英国方面的担忧则源于其对廉价进口食品的长期依赖。《经济学人》抱怨称,粮食委员会计划带有“一个强烈的倾向,那就是使食品平均价格远高于自由市场水平”,而这将“对以商业方式进口食品的国家形成不利”。英国本来就濒临破产,而粮食委员会还会给英国带来高达3 500万英镑的损失。奥尔认为,由于英国的财富是通过“进口当地人生产的廉价食品和原材料而累积起来的,这些当地人的工资却很低,生活极度贫困”,“公平的价格”这个可怕的概念威胁到了“英国的经济繁荣”。奥尔的国际主义长期以来备受怀疑,因为其与英国民族主义者对廉价食品的渴望形成鲜明对比。他声称,英国政府“只想霸占加拿大过剩的小麦,而对其他国家可能会饿死的数百万人不管不顾”。这种平等主义意味着要缓解在全球食品供应中表现出的巨大不平衡,尤其是营养不良和饥荒在地球上的分布。这就动摇了一个未被言明的假设,即发达国家最终应该比全球南方吃得更好。一位英国部长显然对印度人民可能与英国人民有相似饮食而感到震惊。奥尔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1947年,由18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粮食理事会(World Food Council)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其职责是监督和统计。195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迁至罗马,继承了以前国际农业研究所的许多职能。通过信息交流也许可以实现对粮食的管理,但它并不会对世界粮食政治的结构性不平衡产生任何重大改变。
到了1945年,尽管真正全球性的粮食问题已经出现,但美国和英国的国家利益阻碍着任何真正的跨国解决方案的实施。二战前的过度生产被用来稳定世界价格、减少市场波动,并通过向易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欠发达地区供应粮食来平息萌芽中的动荡,从而为美国谋取利益。在食物匮乏的地区,人们非常担心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会蓬勃发展,因此给予或扣留食物的权力成为冷战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承认了食物权。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农业活动咨询委员会宣称,粮食问题是“当今世界许多紧张和动荡的根源”。该基金会将饥饿与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呼吁将西方的农业技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1954年的《美国粮食用于和平法案》(PL480,American Food for Peace Act)则允许美国利用剩余的粮食商品扩大其与友好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这种美国版的全球化生命力,或称“美国谷物力量”(American grain power),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即通过补贴,将资本密集型农业、高产作物和大量的化肥引入被认为易受饥荒和政治不稳定影响的地区,如墨西哥和印度。
尽管绿色革命是美国的倡议,但也应注意到它与英国人所提出的“大星球的哲学”之间存在着明显联系。绿色革命进一步将全球南方的部分地区纳入市场化的全球食品体系,还抑制了社会主义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例如,墨西哥的农业计划就旨在推动本国农业从自给自足转向更大规模的商业农业。为解决南亚粮食保障的长期问题,绿色革命提供了一种矿物质的解决方案:粮农组织从1946年起就开始推动大幅增加化肥投入。于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发生了显著增长: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全世界的谷物产量增加了两倍。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据估计,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人均可直接消费的粮食所提供的热量,从每天2 320卡路里增加到2 660卡路里,发达国家则从3 160卡路里增加到3 410卡路里。最终,绿色革命和其他战后发展项目使肉类、小麦和糖更深刻地嵌入到全球饮食之中,并伴随着相应的情感和意识形态机制(发展、自由和口味)。1952年的一部关于谷物磨粉的历史著作指出,美国的面粉商正在“提高全世界广大落后人口的生活水平,使他们也成了传播自由和启蒙的‘沃土’”。尽管绿色革命取得了成功,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如债务、阶级矛盾、环境破坏等),而且,日益增长的产量增幅是无法无限持续下去的。1966年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世界粮食供应专家小组(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Panel on World Food Supply)的报告指出,人口增长和欠发达地区的粮食供应问题再次卷土重来,并宣布“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解决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专家小组得出结论:“要实现这个创举,就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共同投入,其规模在和平时期的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加州理工学院的生物学家詹姆斯·邦纳(James Bonner)更预言道,“发展中国家的饥饿人口”将被动物化,并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种族或物种”;富人最终将“吞噬”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以补贴的方式向苏联大量倾销谷物,加上厄尔尼诺现象、糟糕的收成以及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峙后油价上涨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自1945年以来首次真正的全球粮食危机。国际小麦价格从1972年中期的每吨60美元左右飙升至1974年2月的每吨220美元。有人预言,廉价食品的时代将走向终结。动荡的小麦市场引发了从西非到孟加拉国的饥荒。对于这些交织的问题,国际社会的直接回应是1974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峰会,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召开的重要粮食会议,会议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粮食安全和增产。然而,70年代的危机清楚地暴露了粮食价格和燃料价格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世界市场持续动荡以及食品系统易受气候冲击影响等问题。这场危机还促使人们重新寻找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以摆脱传统农业的地域限制,如浓缩鱼蛋白、藻类生产和石油蛋白等,但这些技术解决方案最终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成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重组对全球食品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1986年,美国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John Block)表示,发展中国家应该自给自足的观念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因为他们可以从美国购买到更便宜的食物。应运而生的“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政策使发展中经济体向世界市场开放,信贷机构和营销委员会被取消,出口管制减少,市场自由化得到鼓励。这种以去监管化与以出口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战略以及日益全球化的农业食品体系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为了符合“比较优势”,将更多土地转向种植出口作物,导致粮食自给水平下降。例如,埃及和菲律宾已分别成为小麦和大米的主要进口国。从1961年到2001年,国际粮食贸易增长了五倍多。经济发展与粮食供应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英国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反复提到的那样,至今依然显而易见。
2007年,世界粮食体系进入另一个动荡时期,这一系统内部的矛盾暴露无遗。正如贾森·穆尔(Jason Moore)所言,2007年至2008年的危机不过是能源、食品、金融、发展和气候等多重危机的一个切面。越来越多的农田被用于生产生物燃料(biofuel)、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导致粮食和化肥的成本急剧上升。世界粮食体系的经济不对称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联合国大会主席的米格尔·德索托·布拉克曼(Miguel DeSoto Brackman)提请大会应该注意“由发达国家的补贴造成的市场扭曲”。放松管制的电子金融系统和信息经济刺激了对基本商品的加速投机,金融参与者仅为了获利而交易期货,与任何实际物质参考脱节。投机交易逐渐成为常态,其与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007年底,《经济学人》的食品价格指数达到了自1845年以来的最高点,食品价格自2005年以来上涨了75%。若考虑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数字会有所下降,但前景仍然并不乐观。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全球食品系统仍然是依赖于流动,而非储存。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食价格指数显示,自2000年以来,所有粮食商品的价格都在显著上涨,尽管在2010年代初达到峰值后有所回落。这对西方许多人(尽管不是所有人)来说只是相对较小的麻烦,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表明,粮食价格上涨导致1亿人“陷入了营养不良足以危及生命的境地”。到2009年年中,有33个国家面临着“令人担忧”或“极其令人担忧”的食物短缺,其中大多数国家爆发了粮食的骚乱。粮食危机与战争之间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在中美洲、墨西哥、亚洲、斯里兰卡和卢旺达等地,因为粮食问题引发的冲突非常常见。2003年的一项估算表明,有27个国家正在发生与粮食供应有关的冲突。食品系统又一次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散布暴力。乔治亚州民主党议员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在2008年的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一些专家称,这场危机比恐怖主义更具威胁。”
20世纪的廉价食品体制仅在三次重大事件中被打断过:两次世界大战和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世界上食物最便宜的地方仍然是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在英国,从1975年到2000年,食品的实际价格下降了31%。最便宜的食品也是加工程度最高的—饼干、冷冻薯条、冰激凌和薯片。廉价的糖、盐和脂肪能让食品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1994年,美国国内的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7.4%,英国则占11.2%;作为对比,法国和印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4.8%和51.3%。然而,21世纪初的粮食危机证明食品并不一定能一直廉价下去。联合国和华尔街对廉价食品时代的结束表示担忧。 2010年,蒂姆·朗(Tim Lang)提出,廉价食品的时代即将结束,“我们再也无法维持那种‘英国旧有的帝国主义观点’,即我们可以轻松获得食品,其他国家会喂饱我们”。这从来不是什么经济学上的重大失误。休谟就曾对过度廉价表示担忧,而里托斯(Ritortus)更曾抨击科布登的“暗藏危机的廉价”。总之,人们对廉价的批判正在增加。与此同时,不论生产效率如何提高,可耕地面积与人口之比仍在不断下降。地球似乎变得更小了: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边界、限制、阈值和安全的操作空间;已经没有第三个半球可供人类开发了。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每人平均拥有超过1英亩的土地用于食品生产;而今天,这一数字已降至0.6英亩,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至0.4英亩。
与此同时,地球的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几乎已经达到饱和。对食品和生物燃料的需求激增,使得扩大耕地变得更加迫切。目前,农业用地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30%,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扩大。最近对全球土地储备的估计表明,“我们正在逼近极限”,因此对生态系统进行管理势在必行。生态稀缺性正在导致收益递减,而开垦边缘土地的成本正在增加。尽管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同时增加森林面积和农业产量,但最近的一项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是:“‘唾手可得、可自由开发’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了。”尽管生物多样性丧失、碳排放、水土流失和养分循环被破坏的风险越来越大,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此外还有更多关于耕地峰值的乐观估算—有人自信地断言,虽然人们有可能达到耕地的极限,但这可以被推迟到很久以后。任何分析家都必须承认,预测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不过有大量证据可以表明,纯粹的丰饶主义是一种极为危险的立场。
于是,有人又提出了“半个星球”(half-planet)的哲学,试图估计农业或城市扩张的极限:计算表明,如果我们继续保持目前的饮食和扩张速度,到2050年,所有可能的粮食安全生产空间都将被耗尽。这种估计并非马尔萨斯主义的简单复兴。因为空间的计算总是与特定饮食对土地的需求有关,而英式饮食的全球化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所必需的农业用地。英美世界对肉类的偏好,以及为普及这一饮食模式而形成的“大星球的哲学”,继续使土地和资源不断向这些营养转型后的肉食先驱者们倾斜。斯米尔(Smil)精辟地指出:“在蛋白质摄入方面,富裕世界已经明显过剩了。” 增加动物蛋白的摄入意味着进一步加剧牲畜养殖的集约化,以及各种新型“大星球”策略。减少肉类消费,哪怕是适度减少,也能节省大量耕地。
这就是所谓的“新的全球土地掠夺”(new global land grab)的背景,它与富裕的中东和东亚国家的关系尤其密切。这种掠夺和18世纪、19世纪的“商品前沿”如出一辙,为了开发地球空间中剩余的那些“未充分利用”部分(用于生产粮食和生物燃料),他们瞄准了缺乏西方式个人财产权传统的弱小国家和土著地区。对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森林的破坏就是一个例子。非洲被称为“最后的前沿”或者“前沿市场”的所在地,这已经不是一种讽刺了。新形式的“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能将侵占所谓“非洲空地”的做法合理化,只因为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制度不符合西方规范,而且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中,这些土地的比较优势非常有限。这种行为明显是殖民时期的土地征用和种族灭绝的回响。在埃塞俄比亚,人们正从原来的定居点被重新安置到集中的村庄,一些团体怀疑去农业化实际上是一种种族灭绝。伦敦仍然是这类企业的金融中心。某些投资者,比如复兴资本公司(Renaissance Capital)的理查德·弗格森(Richard Ferguson),就对利用这类土地推广工业化农业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这些机构希望将整个世界变成私人资本不受约束地运作的领域,让维多利亚政治经济学得以延续。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投机行为与英国暴力的历史遥相呼应。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蔗糖农场,即由蒂尼·罗兰(Tiny Rowland)及其罗荷公司(Lonrho company)资助的凯纳纳种植园(Kenana plantation,位于苏丹)预算严重超支,最终需要政府补贴才能继续运作。曾由前英格兰慢速左臂旋转投手菲尔·埃德蒙兹(Phil Edmonds)担任主席的荷兰农民生产者协会(Agriterra)则在莫桑比克的养牛业中投入巨资。总而言之,正如纳利所言,这种土地的掠夺“标志着金融市场对食品系统的深入渗透”。
新的全球土地掠夺、廉价食品的潜在终结以及气候变化,这三者是世界农业系统中一个特别复杂的“顽疾”的相互关联的元素。食品危机正逐渐成为一种“悄然的常态”。风险管理专家慕尼黑再保险公司(Munich Re)称,自1980年以来,极端天气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两倍,给世界食品系统带来了严重后果。比如,2011年2月的飓风“雅斯”摧毁了昆士兰的甘蔗田,还有最近肆虐美国、澳大利亚和乌克兰的旱情。水资源短缺也正在威胁着中国和非洲南部的粮食安全。1980年至2003年间,土地退化情况加剧,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土壤形成速率接近于零。氮循环的紊乱也主要由英美世界的国家造成:最近的一项对九个国家氮足迹的计算表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氮足迹最高。无序的城市化、土地利用的变化和大规模的畜牧业为新型病原体的滋生提供了多种新环境,从大肠杆菌O157:H7、疯牛病和禽流感到尼帕病毒、奇昆古尼亚病毒和亨德拉病毒,层出不穷。不过也出现了一套跨国风险管理机构和办法,负责监测来自农业食品系统内部的新威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动植物卫生检疫协定》、食品法典委员会和欧洲食品安全局。
全球营养转型的趋势正在推动生态转型。虽然“所有国家都趋向于肉类、牛奶和甜味剂含量较高的饮食,并从脂肪中摄取30%至35%的能量”的主张似乎已成定局;虽然人类的发展并非只有采取英美的营养转型这一条路可走,但这种历史联系的确存在,且不容否认。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世界红肉和家禽的消费量从1961年的人均49磅猛增至2011年的人均91磅,这一趋势刺激了动物饲料生产的大幅增长,并使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美洲成为重要的肉类出口地区。这种增长要求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虐待动物和劳动者的担忧。目前,全球食品生产排放了全世界约30%的温室气体,而在所有食品类别中,动物蛋白生产造成的环境影响最大。
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地方特殊性,但英国的营养转型正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以更大规模和更快速度被复制。1952年,中国人摄入的蛋白质中仅有3.1%来自动物食品;到1992年,这一比例就增长到了18.9%。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生产国。1946年至1987年间,日本的脂肪消费量增长了近三倍,肉类消费量增长了近九倍,牛奶消费量增长了六倍。麦克马洪(McMahon)也总结说:“令人惊讶的是,像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国家也正在步英国的后尘。”韩国近90%的小麦和玉米依赖进口,这一比例已经高于20世纪初的英国了。
营养转型的深刻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再次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矛盾现象。目前,全球大约有十亿人肥胖,同时也有约十亿人在忍受饥饿。1962年至2000年间,世界人均甜食消费量增加了74卡路里,到2014年为止,全球共有4.22亿人患有糖尿病。尽管对全球饥荒的管理得到显著改善,人道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但非洲许多地区仍然严重缺乏粮食保障。2017年,英美两国在也门实施的封锁显然是导致人道主义危机迫在眉睫的原因之一。食品控制是巴以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沙地带处于长期的封锁状态,并被强行“去发展化”,严重依赖国际援助。2006年,曾有传言称,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的一位顾问表示:“我们就是要让巴勒斯坦人饿肚子,但又不能将他们饿死。”这种能控制的半饥饿形式表明,发达国家拥有着至高无上的食物权。地球上的农业食品系统和经济结构将食物不成比例地导向发达国家,就像19世纪晚期的大英帝国所做的那样。19世纪食品体系中固有的、深刻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也延续了下来。与成年男子相比,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女童)更容易身体虚弱、疲乏和饥饿。全球饥饿人口中约有70%是妇女和女童。每天约有一万六千多名儿童死于与饥饿有关的疾病。饥饿会导致发育迟缓和认知发育受损。对穷人、弱者、妇女、非白人族裔、动物和生态系统施加缓慢暴力的这种关键的权力关系,正以全球化的方式展开。

(本文选摘自《环球共此食:工业化英国、食品系统与世界生态》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