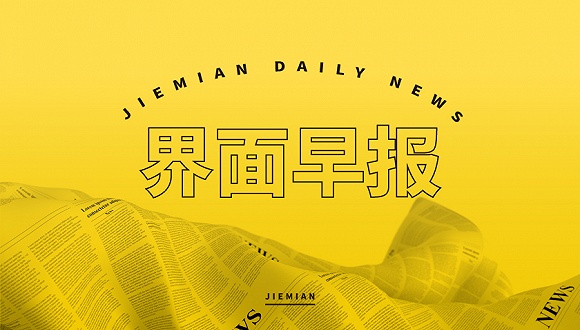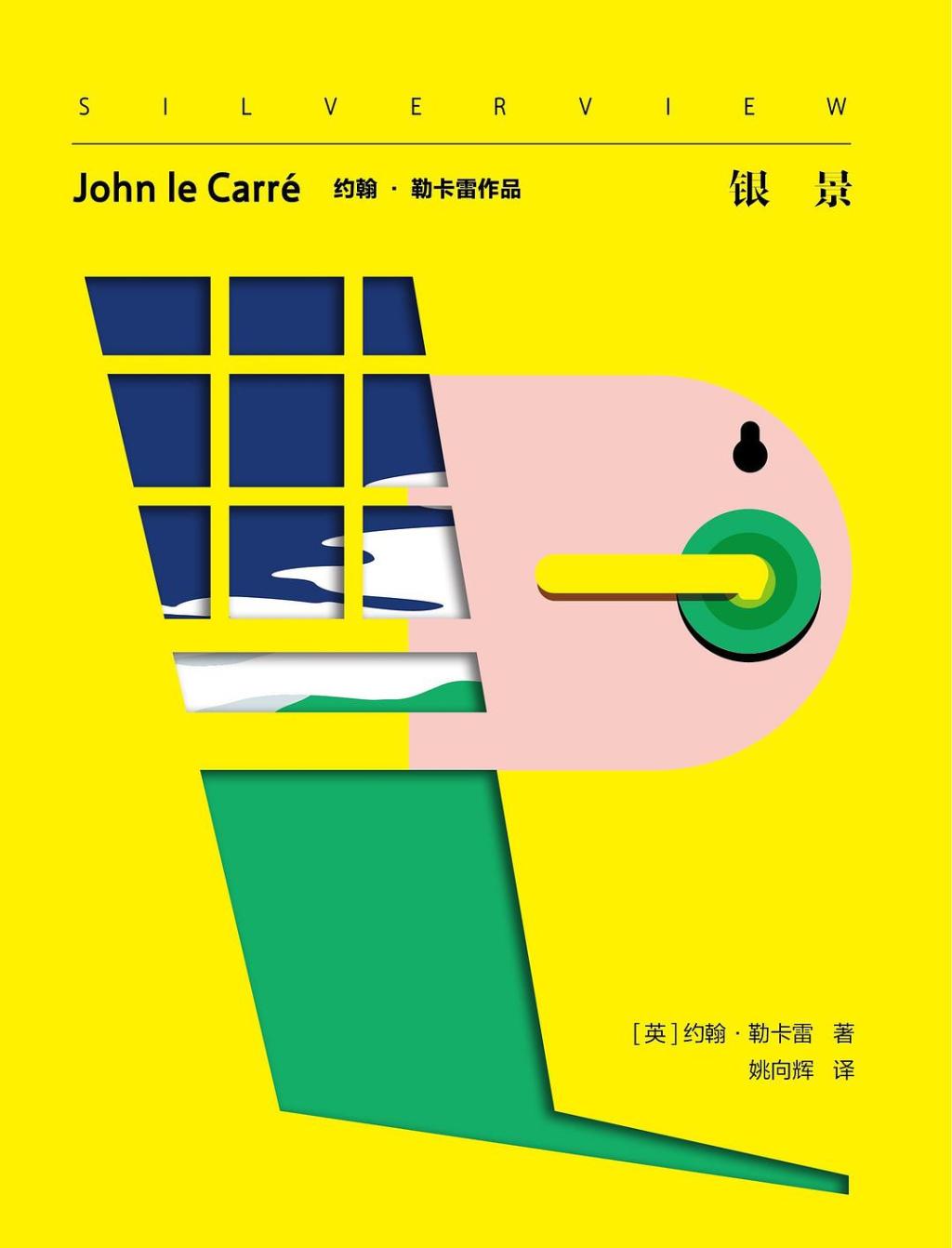
[英]约翰·勒卡雷著,姚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264页,68.00元
2020年12月12日,八十九岁的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去世。和很多老人一样,一起意料之外的跌倒事故导致了这桩死亡。相较于“大卫·康威尔”这个陌生的名字,老人的另一个名字“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更为世人所熟知。在去世近一年后,他的遗作《银景》(Silverview)正式出版,成为这位冷战时代最知名间谍小说家的遗作。

约翰·勒卡雷
《银景》的故事以双线叙事的方式推进。一边是主角朱利安·劳恩斯利,一位逃离伦敦来到偏僻海边小镇开书店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位神神叨叨的老人,名叫爱德华·埃文。这位老人声称是朱利安父亲的老相识并表示愿意给书店经营出谋划策。于是,这一老一少围绕书店的交往,牵出了一桩延续数十年的谍海往事。故事的另一个主要角色普斯图尔特·普罗克特则是一位新时代的情报局官员,试图寻找组织内部的漏洞。一系列线索将他引向了“银景”所在的这座小镇。
在这部篇幅并不算长、两百余页的小说中,读者依旧能读到勒卡雷作品中绵长的主题和无尽的虚无感。前者关乎冷战时代的忠诚与背叛,后者则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银景”源自小说中海边小镇附近某栋别墅的名字,而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勒卡雷自己晚年的生活状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就从伦敦搬到了英格兰西南角康沃尔郡的圣伯里安。勒卡雷的别墅位于兰兹角,一处被大西洋、英格兰海峡三面包围的偏僻角落,那儿是被认为是英格兰岛的最西端。据说勒卡雷的别墅紧挨着长达一英里的悬崖,海浪与大风成为他晚年最常体验的风景。在《银景》中,那位退休多年、看似隐居在海边庄园“银景庄”里的退休老间谍爱德华·埃文,自然会让读者想到同样躲在悬崖边别墅中的勒卡雷自己。
将《银景》置于勒卡雷庞杂的创作序列中,就能发现其如何延续着作者长期关注的母题,以及有什么特殊之处。首先故事的舞台非常小,基本就是围绕“银景庄”及其所在的小镇,伦敦又或是其他场景也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然而,《银景》所触及的历史背景又极为宽广,从冷战高峰时代的东欧一直延展到冷战结束后的巴尔干。实际上,《银景》似乎也是对勒卡雷笔下典型人物的一次“总结”: 朱利安,一个被卷入间谍世界的普通人;爱德华·埃文,一个经历神秘、狡猾且多变的老间谍;普斯图尔特·普罗克特则像是一个“二十一世纪低配版”的史迈利,试图挖出组织内部的“内鬼”、“鼹鼠”。然而,不同于《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视角,《银景》并不想讲一个“史迈利们”如何找到“鼹鼠”的故事,而是想从另一端讲述某类人为何会选择成为“鼹鼠”的故事。或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勒卡雷才没有在《银景》中给出一个如《锅匠、裁缝、士兵、间谍》那般明确的结局。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创作上的原因。
依照勒卡雷的儿子尼克·康威尔在后记中的说法:《银景》创作于2012年前后,但他的父亲生前刻意搁置了这份书稿,以至于在他书桌的抽屉里静静躺了近十年之久。勒卡雷似乎对这部小说始终心存疑虑,多次修改却仍不满意。这或许也是《银景》篇幅相对较短,结局又非常暧昧的另一大原因。如果对照勒卡雷于2017年出版的另一部晚年代表作《间谍的遗产》,或许有助于我们看清勒卡雷晚年的创作心理以及为何会“心存疑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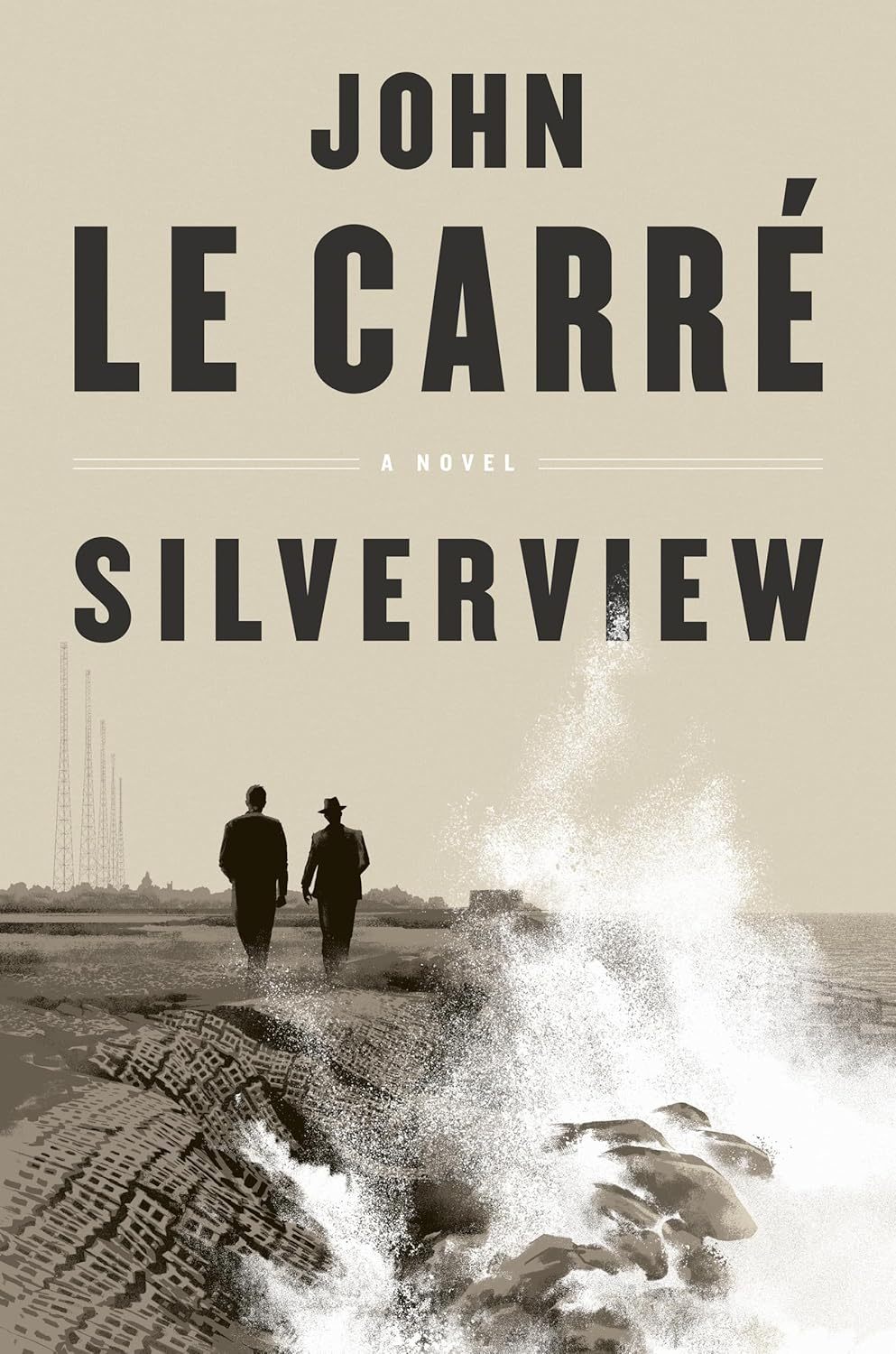
《银景》英文版
单就主题而言,这两部小说似乎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间谍的遗产》与《银景》都是对过去的清算,只是角度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小说都在描绘新时代与冷战岁月的格格不入,新时代的“间谍们”完全无法与自己的老前辈们共情。勒卡雷在冷战时代创作的那些故事中,无论是身处哪个阵营,无论是选择忠诚或背叛,似乎都基于某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可以是来自或左或右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是来自私人情感(例如爱情),又或是纯粹的人道主义情怀。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勒卡雷笔下那些当代情报局的“间谍们”或“官僚们”,已经无法理解前辈及其对手究竟是为何而战。对他们而言,情报工作不过是一份需要按时交差的营生,而非是需要用生命捍卫的伟大事业。
冷战时代的理想主义早已灰飞烟灭。
众所周知,间谍的工作就是“欺骗”:假身份、假关系、假忠诚。他们会背叛信任他们的人,同时也随时可能被自己的组织所背叛。模糊的灰色地带、各种背叛的无尽循环构成了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但这些间谍故事的设定背后,勒卡雷希望讨论的始终是:极端环境下,人们的道德选择。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不是在写间谍,我是在写人。只不过这些人恰好是间谍。”而冷战时代的明争暗斗,更为了这类道德选择添加了天然的戏剧张力。但无论如何,勒卡雷在描绘这种“张力”时更愿意为其涂上“理想主义”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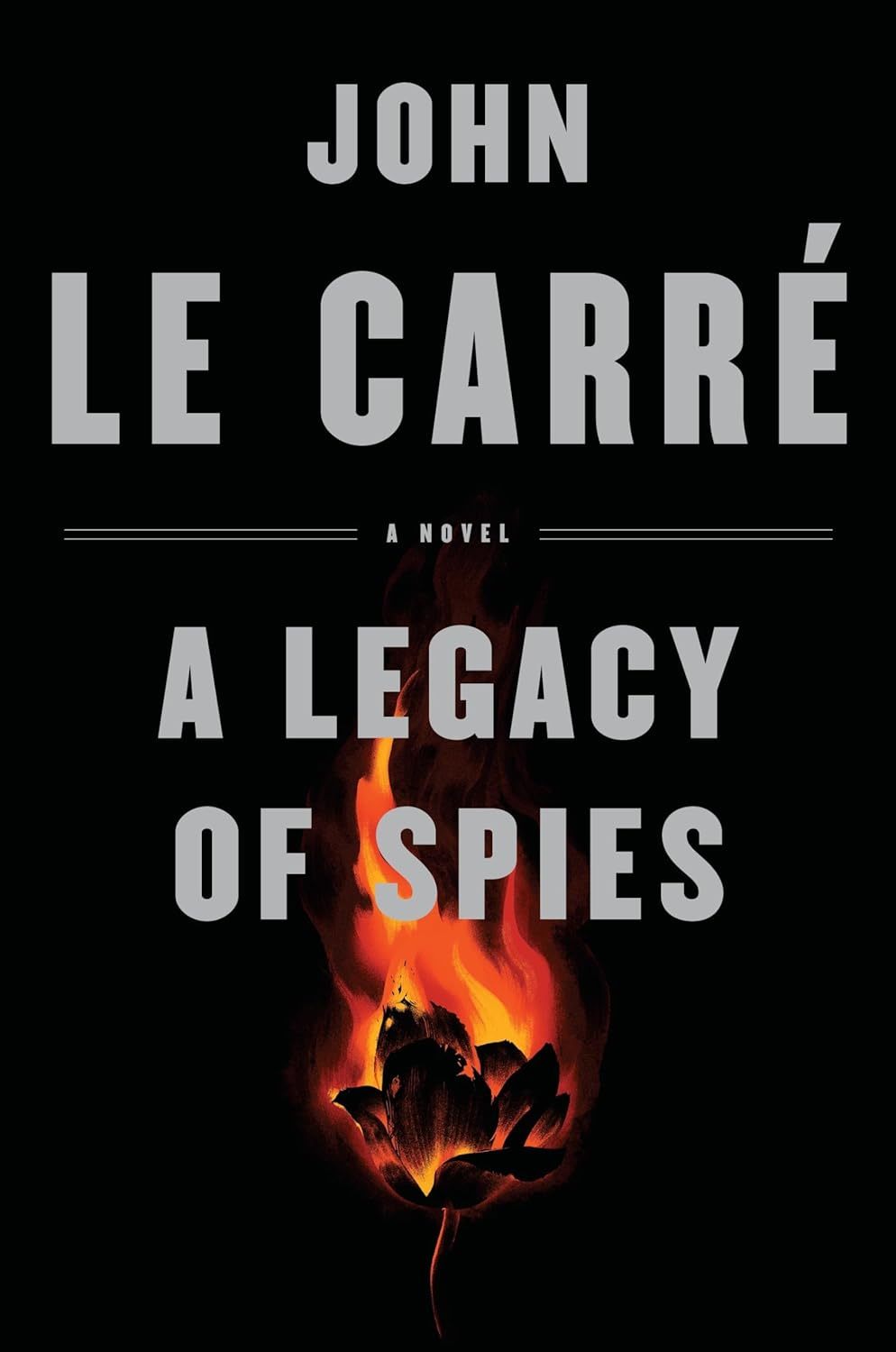
《间谍的遗产》
2017年,在出版《间谍的遗产》后,当时已经八十六岁的勒卡雷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当下时代的忧虑。他认为英国脱欧是对欧洲理想的背叛,而民粹主义的兴起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在他看来,史迈利这一代人所捍卫的“欧洲精神”——理性、宽容、人道主义——正在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所取代。这种失望的情绪与理想破灭后的虚无感,同样出现在《银景》的字里行间。
当铁幕落下,老间谍们发现自己成了无用之人。当年分处东西阵营的他们曾各自为某种信念而战,如今却发现这些信念都已经无人问津,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银景》中,勒卡雷将这种失望与虚无感浓缩在那家主人公朱利安·劳恩斯利开的小书店里。爱德华·埃文建议朱利安在书店里设立的“文学理想国”显然是某种对过往时代理想主义的哀悼与怀念,尽管这个理想主义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至于普罗克特捉“鼹鼠”工作同样谈不上成功,但这并不是我称其为“低配版史迈利”的原因,而是因为他缺少史迈利的道德感与理想信念。小说中,普罗克特无疑便是“支离破碎的情报局”的具体化身。用尼克·康威尔的话来说,就是“它不再能够确定自己的正当性了”,“也失去了对国家代表着什么、我们对自己身份的确定感”。
合上《银景》,就会想起《间谍的遗产》中重新登场、年逾百岁的史迈利在小说中曾讲过那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欧洲人。”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勒卡雷本人透过史迈利之口讲出的。晚年的勒卡雷想留给世人的不仅是精彩的间谍故事,更是他对一个时代的见证、反思与缅怀。在如今这个日趋复杂且越来越极端的世界里,那些过于简单的答案往往是最危险的。而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其能够呈现这种复杂性,让我们在灰色地带中寻找践行各自道德价值的可能,而不是被某种极端思维所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