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有高下之分,那么在一百多位获奖者的长长的名单中,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一定位居前列。世人所熟知的让-保罗·萨特、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钱钟书等名人大家都曾受到莫氏的影响。翻开莫里亚克的小说,人类的罪恶和痛苦几乎无处不在,这成了莫氏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如《给麻风病人的吻》(1922)中长相丑陋、被不幸婚姻束缚、之后染上重疾临死时发现医生对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欲图不轨的绝望的让·贝鲁哀尔,又如《爱的荒漠》(1925)中被土豪拉鲁塞尔包养、又把邻居古雷热父子迷得神魂颠倒的玛丽亚·克罗丝,再如《蛇结》(1932)中从年轻时就嫉妒妻子对其他男人的恋情,终其一生都以冷酷、刁钻、狡猾的态度对待家人的大财主路易,还有《苔蕾斯·德斯盖鲁》(1927)中那个试图毒杀丈夫的同名女主人等等。
对此,莫里亚克本人曾自我揶揄道:“每次法国有女人想要毒死自己的丈夫或勒死自己的情人,人们就会对我说:‘这个主题很适合您……’,在世人眼里,我成了经营罪恶主题博物馆的馆长,我的长项就是描写魔性的人和事。”然而,他纵身人性的弱点和邪恶之中,并非出于追求艺术绝技的狂热。即使在他无情地分析现实的时候,莫里亚克也始终确信,有一种超越理解的爱。他曾十分简要地宣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够变得比目前更少一些罪恶。”终其一生,莫里亚克都忠于已经化为自己血肉的真理,竭力按照人物的本来面目看待和描绘他们。这些人物将悔恨交加,希望自己变得即使不是更好,至少更少一些罪恶——就像博物馆展陈的各式各样的艺术品,或许总有某一件能给某个人以启迪和反思。莫里亚克的小说就像一个窄口的深井,能让人在底部看到一泓神秘的活水在黑暗中闪烁。

莫里亚克
冷酷的恨意
莫里亚克193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蛇结》被公认为是其巅峰之作,人性中冷酷的恨意在此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部罪恶主题的杰作同时展现了莫氏炉火纯青的叙事技艺:小说以控诉书开篇,渐次转为忏悔录,最终升华为回忆录的奇特结构。故事始于叙述者路易写给妻子伊莎与子女的信。他设想此信藏于保险柜文件证券间,待自己入土后家人争产时被发现。字里行间浸透着仇恨、怨毒、愤怒、委屈、指控与失望,佐以精心粉饰的合理化辩解,令家人读来愈加苦涩。随着叙事的推进,这封遗书逐渐蜕变为忏悔录式的日记,路易借此追溯过往,探寻当下自我厌恶的根源。伊莎在他完成这封恶毒“致歉信”前离世,而这场剖白最终成了路易自我救赎的序章。
小说伊始,路易坦承此信是酝酿数十年的复仇之举。他告知家人:若愿意,随时可剥夺他们翘首以盼的财富——这份令他牺牲一辈子的资产。他承认这些牺牲“毒害”了心智,“滋养喂肥”了心中的“毒蛇”。“我天性如此,”他冷冽自白,“生来便是扫兴之人”。要知道,独子路易幼年丧父,母亲虽有慈爱却不解其心。他艳羡他人珍藏童年回忆,自己却只有牺牲与疏离的烙印。加之社交方面的笨拙和孤僻,让他最终沦为猎艳之徒,只求肆意羞辱掌控。“我是野兽,”他坦言,并为此付出且持续付出代价,但此刻无悔。
在长篇控诉中,他告诉伊莎:最令他着迷的是她竟觉他“不再可憎”。因一场误会,伊莎婚后向丈夫坦承曾与罗道夫相恋。读者如旁观者清:伊莎此举意在敞开心扉,避免秘密横亘彼此。路易却认定罗道夫阴魂不散萦绕着他们两人的婚姻,坚信伊莎仍暗恋此人。有了这样的误解后,路易开启所谓“大静默时代”,余生无视伊莎。她自然转向子女寻求温情,反加剧路易的怨恨。他堕入隐秘的放荡生活,对处于“幼蛆阶段”的子女漠不关心。孩子们终生承受父亲的憎恶与冰冷疏离。后来路易成为巴黎名律师,法庭上的雄辩令报纸杂志纷纷邀他撰稿,政界则劝他参选。对此他嗤之以鼻,坚称只为持续赚取“大钱”。
种种的失望与误读伴随路易对人生败局的剖白。他告诉伊莎:自己饱受“生命毫无所得”的折磨,除死亡外“无所期盼”,他不信彼岸世界,也不见解决之道。他懊悔人生的抉择皆是错误,而且终其一生都真正学会生活。“我知道自己的内心”,他写道,“那是毒蛇之结。”到小说第二部,这封已演变为笔记的信件,被路易无意携带前往巴黎寻找私生子罗贝尔。与家庭彻底决裂后,他承认将吕克与菲利的特质投射于罗贝尔身上,对这两位家人他依旧怀有隐秘的温情。路易启动寻子计划,源于偷听子女怂恿伊莎将自己送入精神病院。为寻求报复,他决意将全部遗产赠予罗贝尔,意图再夺走家人所珍视之物。
路易回忆起一幕:伊莎受子女唆使,询问她嫁妆中的股票份额。他保证股票安全,伊莎崩溃质问其为何那么憎恨子女。他则开始咆哮:“是你恨我!更准确说,是我的孩子们恨我!你只是无视我!”伊莎向丈夫坦白:婚姻存续期间,她从未让子女和自己一起睡,因始终期盼路易某天晚上或会回到妻子身旁。两人关系对彼此的摧残至此也展露无遗,可是如今再想修复却为时已晚。后来伊莎离世,路易则如此悲叹:“她到死都没有看清真正的我,她并不知道我不仅仅是她所想象的怪物与施虐者。”人性的可悲可叹,尽在其中。
最终,人性中的悲悯和理解占据了上风:菲利抛弃妻子雅妮——即路易的孙女。洞悉家族苛待菲利而雅妮则痴心未改,路易便安慰孙女并问道:“你真认为菲利值得你承受‘苦痛和折磨’吗?”无人知道答案——讽刺的是,路易猝死于笔记书写之时。小说以两封信结尾,其中第二封是雅妮写给叔父于贝尔的,信中她为祖父辩护,称他是所知最虔诚之人。她指其他家人表面虔敬却从不以原则约束生活,盛赞路易毕生践行心中认定的真理。在评述路易一生的结尾时,她这样诘问:“是否可以说于他而言——财宝所在之地,正是他心灵缺席之处?”莫里亚克把这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留给了每一位读者。
无爱的残忍
“我这无谓的生命——我这虚无的生命——这无尽的孤独——这毫无出路的命运。”《苔蕾丝·德斯盖鲁》扉页上的这句心灵自白,或许可以概括这个悲剧性女人的一生。这位生于法国阿尔热卢斯豪门望族的女子,成了豪门联姻的情感牺牲品。从一开始,莫里亚克就知道苔蕾丝就是戴着面具的古罗马毒妇——圣罗库斯特。苔蕾丝原本应该是一个快乐的女子,所有的人看到她那特有的微笑,都会说“甭管她长得是美还是丑,您只会觉得她有魅力。”作为彼时高中生的苔蕾丝一直喜欢读书,或者是阅读在苔蕾丝身上留下的印记: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魅力。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却成了中国读者口中的“法国潘金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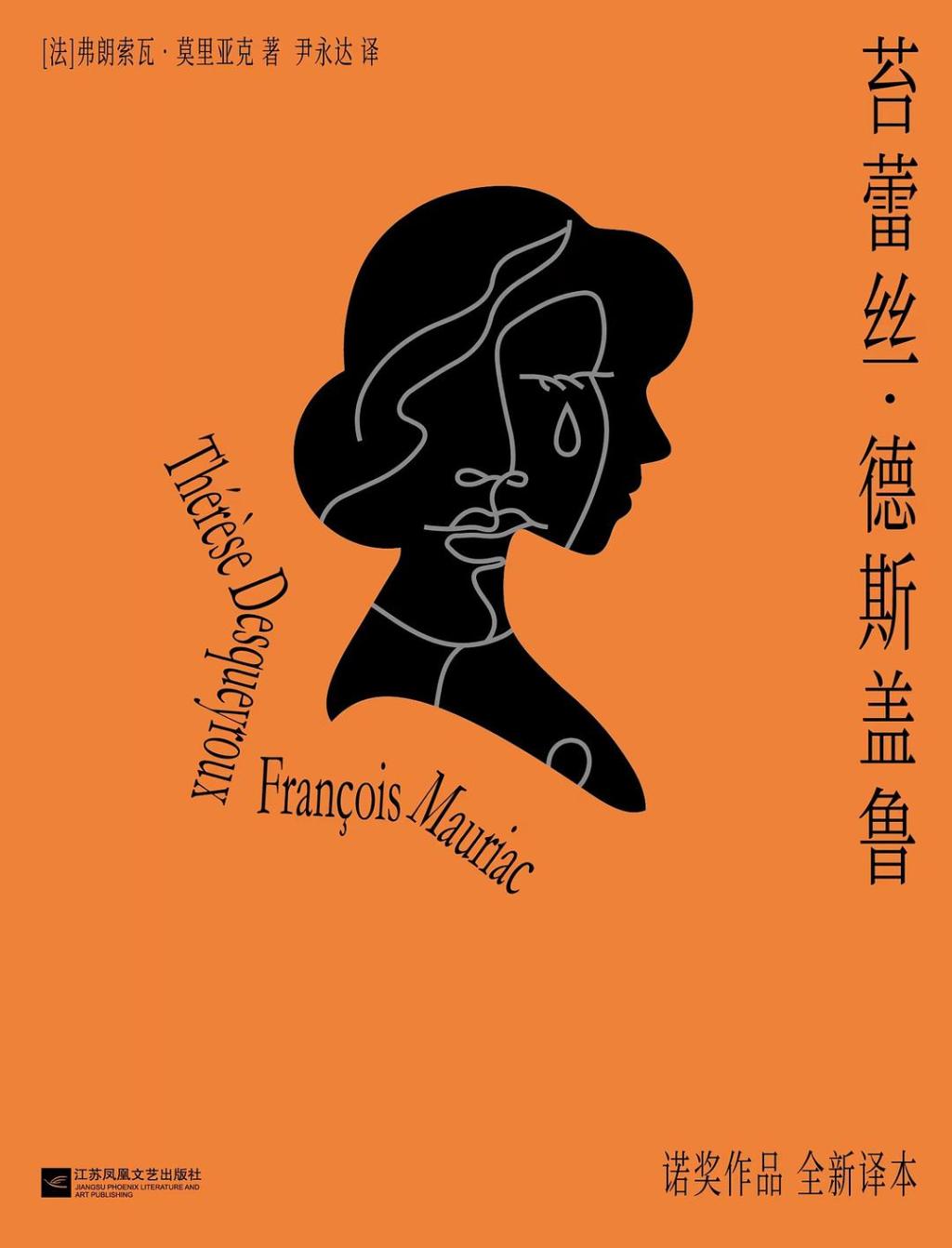
《苔蕾丝·德斯盖鲁》
这位企图毒杀丈夫的苔蕾丝经历着一种觉醒之后却无法改变的痛苦。苔蕾丝做梦也想摆脱与贝尔纳的无爱婚姻,她无法忍受对方的粗鄙和无知。可是,彼时的时代和基督教文化,让她根本无法摆脱这段噩梦般的婚姻。于是,她麻木地看着贝尔纳往水杯里滴药水,却没有张开嘴去提醒——她是被动的圣罗库斯特。这种麻木的残忍源于无爱的痛苦,十分渴望爱情的苔蕾丝对自己完全不爱的贝尔纳充满嫌恶,但还没有到要杀害贝尔纳的程度,但她内心的麻木的残忍阻止了她去告诉贝尔纳水杯里药水滴多了。她或许有杀人动机,那张药方或是证明——苔蕾丝曾想喝下药水求得解脱,可她姑姑的意外去世拯救了她。
贝尔纳的报复是如此狠毒,苔蕾丝被囚禁,被禁止与女儿小玛丽见面,甚至连家里的佣人也对她冷漠以待。如果不是家族利益的牵绊需要苔蕾丝继续活着,瘦脱相的苔蕾丝早就被折磨致死了。正是这份撕裂感,使苔蕾丝在遇见让·阿泽维多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与转折。让直言不讳地揭露了她的处境:“在这里,您不得不说谎,一直到死。”与他短短数次的见面,却足以将苔蕾丝的身体和灵魂引向另一个世界——巴黎,那里的法则是“成为自己”。让离开后,苔蕾丝体会到了真正的寂静。她仿佛“走进了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陷入了越来越浓的黑暗中”。让之于苔蕾丝,如若她理想的“镜像”。
如果说在遇见让之前,孤寂尚能忍受,苔蕾丝还试图在家族与自我之间找寻平衡,那么是让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久违的理解与自由气息,并推动着她“像个野蛮人一样,不加思考,走出黑暗,走出厌恶,抵达自由的空气,快!快!”这份冲动成为“去过危险的生活,在深层意义上”的最为生动的诠释:危险并非指外在的冒险,而是敢于突破既定秩序,直面自我与自由的深渊。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去了巴黎的苔蕾丝,能幸福吗?“她独自笑着,像个很幸福的人”。这份“像”本身揭示了虚妄:她固然在表面上摆脱了旧有社会环境的束缚,却从未真正挣脱那分裂、冲动而受伤的本性。莫里亚克只是“相信在此地,你至少不会感到孤独。”
小说的最后,苔蕾丝“离开车辙”。在巴黎的街头,她微带醉意,走向了一段全新的、亟待创造的人生——“我珍爱的,不是石头砌成的城市,不是研讨会,不是博物馆,而是那片躁动不安、生机勃勃的森林……阿尔热卢斯的松林在呻吟,之所以动人,只是因为它听起来像人的声音。”她明白自己不愿或不再愿意的是什么,却依然不知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莫里亚克最终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没有给予这个“怪物”真正的救赎,而是让她继续沉溺在那混乱无序、分裂且有罪的天性中,“漫无目的地走着”。
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苔蕾丝同样承载着莫里亚克自身的精神投射。与其说他在塑造一个虚构的女性,不如说他借苔蕾丝与自我对话,探索人类灵魂在压抑、孤独与罪恶中的可能出路。这份执念也体现在他对苔蕾丝命运的不断“续写”上。继《苔蕾丝·德斯盖鲁》之后,莫里亚克又在1933年发表了《苔蕾丝在诊所》《苔蕾丝在旅馆》两个短篇,并在1935年的《黑夜的终止》中进一步追踪她的命运。苔蕾丝成了莫里亚克创作中的特殊存在,负载着作者对精神困境与救赎命题的持续而未竟的思考。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其目的是警醒世人。之于莫里亚克,他正是通过苔蕾丝这个悲剧性人物来实现自己的这一现实抱负。
异化的疏离
“你恨一个人多年,从未放弃过复仇,竟碰上了,那该怎么办呢?”这是让莫里亚克声名鹊起的小说《爱的荒漠》的开头。故事正是从雷蒙·古雷热在巴黎的酒吧偶遇故人玛丽亚·克罗丝与维克多·拉鲁塞尔开始说起,十七年前的回忆涌上心头。古雷热一家人看似每天生活在一起,家人之间却有一种有如荒漠般的疏离感。雷蒙与医生父亲保罗·古雷热生活在优渥的中产阶级家庭,却因生活的平淡与厌倦,竟爱上了同一个女人——玛丽亚·克罗丝。玛丽亚是个不事劳动的文艺女青年,她被波尔多豪贵拉鲁塞尔包养,但在道德层面却需要“好人”保罗·古雷热医生的慰藉和鼓励;雷蒙则在心理上接近与自己亡儿年龄相仿的玛丽亚,然而这两种精神寄托最终都以幻灭告终。父子俩在情感的荒原里徘徊,那种无法被理解的疏离感,像极了现代人深夜刷手机时的空荡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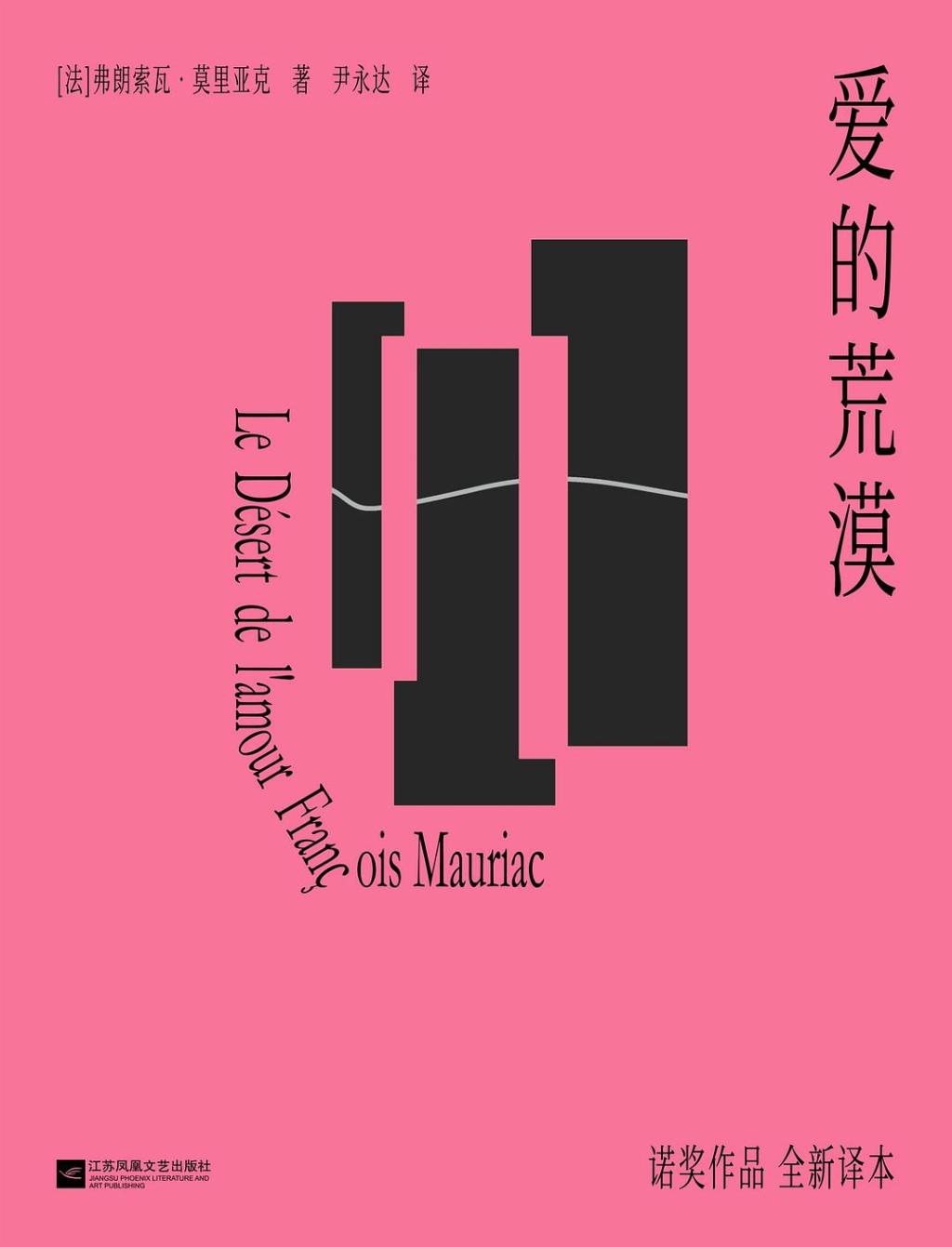
《爱的荒漠》
玛丽亚的儿子弗朗索瓦死了,虽然邻里到处传玛丽亚的丑闻,但她为了不想让他人指责自己被包养,卖掉了马车,开始坐电车,这才有了与雷蒙的电车相遇。而雷蒙在遍历了出逃与自杀的种种念头后,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遇到玛丽亚,才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正是与玛丽亚的相遇,让雷蒙成为了十七年以后的他,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实则爱的伟力蔓延生发,直抵生命的深处。“我们都曾被爱我们的人锻造并一再锻造,只要他们坚持不懈,我们就会成为他们的作品——他们自己未必认可的作品,他们始料未及的作品。任何爱情和友情穿过我们的生命时,都会留下永恒的一笔。”
玛丽亚就是这样一个很神奇的寡妇,她让圣人犯错,让激情复燃。雷蒙的父亲古雷热医生也深深爱着她,却被玛丽亚拒绝了。她给古雷热的信中写道,“莫里斯·梅特林克恰如其分地总结:‘终有一天,这一天并不遥远,人们的灵魂将不需要肉体的介质就能彼此相知’。”正如帕斯卡所言:“心灵有自己的逻辑”。父亲开始给自己的失败找理由,“失败的人偏要巧妙地粉饰自己,那是人性的终极缺陷,简直像是把身上搓下来的污秽当成宝石来欣赏”。玛丽亚知道医生是什么样的人,她很尊敬他,反而让医生感到绝望。古雷热医生赌过输过,不必追悔,但仍旧对玛丽亚心有所属耿耿于怀。
“既然不能把什么都表达个明白,那就等于什么都表达不明白。”古雷热医生在心中自己是这样编排话语的,“他们不需要我。一个被活埋的人,只要有点儿力气,他有权掀开让他窒息的石块儿。您无法测度横在我和这个女人,这个女儿以及这个儿子之间的荒漠。我对他们讲的话甚至传不到他们耳中。”然而另一边,玛丽亚却也无法接受少年雷蒙,她认为自己已老、已堕落,而雷蒙的纯真与年轻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阻挡了她的欲望。就这样,在这片满是疏离感的“爱的荒漠”中,三个人各自寻觅、苦苦挣扎、渴求着理解与救赎,却又彼此埋怨、徘徊不定,最终迷失了方向。
无涯的时间过去了,很多发生的事情不为人所知,他们曾经在爱情中做了多么疯狂的事情,在十七年以后,只剩下了“可笑”二字。雷蒙永远不会知道玛丽亚曾经为了他而自杀。世间很多事情过去了,就掉入了时间的黑洞里,没有什么真相大白的大结局,只有充满谜团的深渊。雷蒙回忆起电车中的场景,所有爱情来临的时候,永远是“人生若只如初见”。雷蒙发觉“他以前所占有的东西毫无意义,只有他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才有价值”,原来“一个人会被动地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占有如此重的分量”。
归根到底,这份“爱的荒漠”中的深深的疏离感,来自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其中潜伏着强大的异化力量。这部为莫里亚克赢得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杰作最精彩之处,正是对人物内心世界与法国外省压抑的社会氛围的交织呈现,书中的每个人似乎都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原罪——异化的疏离。对于阅片无数的现代读者而言,父子俩同时爱上一个情妇的剧情或许仍然过于狗血,但莫里亚克的眼光始终是冷峻甚至残酷的,他借古雷热医生之口告诉我们:
生活总是令人们措手不及:从少年时代起,他心仪的对象就几乎全是陡然消失的,要么是被别的爱情席卷而走,要么就是寻常的搬家、离开这座城市然后音信杳无。死亡不会夺走我们爱的人,相反,它替我们保留着,将他们永远定格在可爱的青年时代:死亡是盐,可以储存爱情,生命才会将爱情稀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