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2日至9月25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二十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开幕。今年研讨班的主题是“环境史、资源史与人类纪概念”,并作为中法环境月活动之一举办。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学生参与了本次研讨班。

与会者合影
9月22日上午,第二十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正式开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肖琦主持开幕式,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王度(Joan Valadou)、教育领事Benjamin Demiere、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孟钟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Maurice Aymard、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荣誉会长端木美、秘书长乐启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朱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业务主管孟雨等出席了研讨班开幕式。在四天的研讨中,与会学者带来了六场别开生面且展示人类纪问题学术前沿的报告。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莫里斯·埃马尔(Maurice Aymard)教授通过一场主旨演讲拉开了研讨班讲座的序幕。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纪这一新出现的学术名词,他选择以“历史学如何面对人类纪研究的多重学术挑战”为题,介绍该领域研究的概念、起源、发展历程与挑战。人类纪的概念来自1922年的一位俄罗斯地理学家,他最初将之定义为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地球的改变。此后直至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大气学家Paul Joseff Crutzen和生物学家Eugene F. Stoermer才提出了科学的定义。两位学者的论文登上《自然》期刊,标志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的认可——将“人类纪”作为地球地质年代划分的重要节点,愈发关注人类如何显著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环境。这也是本届研讨班选择以人类纪和环境史作为讨论主题的原因之一。人类纪以18世纪末蒸汽机的发明和煤炭能源的广泛使用作为最新的分界点,因为这标志着人类开始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并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埃马尔教授借助两极冰层采样的二氧化碳检测数据,阐释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能够跨越大陆,甚至影响到遥远的南极这一观点。相应地,这也意味着人类纪研究需要具备全球视角——研究不应仅限于某个国家、地区或大洲的特定情况,而是应从全球范围审视人类活动的影响。联想到非洲或大洋洲的某些地区,尽管它们可能并未直接受益于法国或德国的工业革命,但它们无疑受到了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变暖,以及农业集约化和化肥大量使用所引发的环境灾害的日益频繁的影响。
继起始部分的讨论后,埃马尔教授详细解释了人类纪问题如何与历史研究跨学科地联系起来。他指出,人类纪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广泛,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对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全人类却必须共同承担污染的后果,且消除这些影响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这要求历史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与自然科学家并肩工作,以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相关研究。面对这个宏大且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需要提供答案。然而,跨学科研究也带来了两大挑战:首先,一些自然科学家反对使用人类活动影响这类难以量化的概念来划分时代;其次,部分学者认为现在对人类纪问题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埃马尔教授特别强调历史学界需要认真对待人类纪问题。历史学家通常基于现有的理解来研究过去,以此加深对现实的认识,因此他们往往避免对未来进行预测——这与人类纪所要求的对未来的探讨形成了矛盾。尽管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坚持“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的观点,但科技的进步已经帮助我们获得了大量的非文字史料,从而扩展了研究的时间范围。或许我们应该以更加乐观的态度来看待人类纪以及地球的未来问题。最后,教授总结道,人类纪问题揭示了一个事实:从新石器革命开始,技术的进步逐步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尽管过程中有挫折和倒退,但总体趋势并未改变。布罗代尔也曾探讨过新石器化带来的革命性转变,他认为人类从单纯的狩猎者转变为生产者,通过种植作物和驯化野生动物,提高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占有能力,同时也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实际上,对作物品种的干预一直持续到哥伦布大交换:南美洲与欧亚大陆的作物基因库因这一过程而变得更加丰富,这不仅缓解了南美洲的饥荒问题,也帮助欧洲解决了作物病害问题。埃马尔教授的主旨演讲为我们理解人类纪概念及其研究现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9月22日下午,来自巴黎-西岱大学的乔瑟·哈罗伊(José Halloy)教授做了题为“人类纪与存有动植物生命体的地球:地球超长时段历史中多种形态人类社会的出现与存续”的报告。他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其研究展示了简单的活动如何影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这也是多学科合力解决人类纪问题的一次新的尝试。在19世纪,生物学家提出了“新陈代谢”这一术语,用以描述生命体通过物理、化学、生物化学过程维持存在与发展的机制。在探索人类技术系统的构成与演进过程中,哈罗伊教授借鉴了这一概念,以研究科技的迭代与升级,并尝试将其作为理解自然与人类技术系统相互作用的分析工具。实际上,他的方法可以看作是20世纪社会学家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解释城市生态——包括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与管理——的延伸。在详细阐述分期概念之前,哈罗伊教授首先强调了人类活动与地球生命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地球生命的一部分,人类与其他生物共享着相同的祖先和遗传连续性,且同属一个综合的系统;然而,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逐渐改变了与地球生命系统的关系,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化石能源开采和利用打破了地球原有的能源积累周期。在研究地球大气和海洋变化的过程中,NASA观察到人类活动在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中起到了加速作用。这一趋势无可避免地指向了一个结论:人类的发展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为了深入了解其原因,哈罗伊教授认为必须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重视角来研究人类纪问题。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密切联系提醒我们,人类纪问题不仅是一个需要跨学科研究的环境史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未来人类发展道路选择的重大问题。
哈罗伊教授将人类漫长历史划分为七个能源转型阶段。在人类出现之前,微生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并释放氧气,从而改变了地球环境,为地球生命系统的演化奠定了基础。光合作用,或者说自然新陈代谢系统的出现,因此被视为第一次能源转型。随着生物进化和植物的出现,树木通过光合作用积累的能量,成为人类最早可利用的资源;同时,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运动和化学作用,植物的生物能转化为矿物能源。可以说,树木是化石能源时代出现的先决条件。第三次能源转型则是火的使用和石器-铁器工具的出现。工具的出现标志着有机物与无机物的结合,使得人类有能力初步利用自然材料改造环境。前工业化时代的最后一次能源转型始于新石器时代。随着新石器革命,智人得以发明农业并驯化动物——在非洲、南美、欧洲、亚洲几乎同时出现类似现象,时间差不超过几万年。这使得人类能够稳定获得由光合作用系统产生的能量——通常以粮食和肉类的形式出现。之所以称其为前工业化时代最后的转型,是因为直到19世纪前,人类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依赖自然新陈代谢系统获取食物的模式。
18世纪末,人类开始大规模开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加速了地球环境的变化。化石能源时代的进入与终结,构成了能源转型的最后两个阶段。化石能源带来了“爆炸性的”推力——它们单位质量蕴含的能量更大,使得人类各种活动不必再受能源的制约。以1778年的布冯铸铁厂和1887年建造的埃菲尔铁塔为例,铸铁厂的年产量仅为375吨,而埃菲尔铁塔的建设总共需要9000吨钢铁——这相当于铸铁厂产能的20倍。铸铁厂之所以产能低下,是因为在18世纪末,普遍使用的燃料还是木材,其燃烧效率远不及煤炭。因此,尽管每年需要12亩的木材,也只能转化为相对较少的产能。到了1887年,随着化石燃料的普及,大规模冶炼钢铁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化石能源对人类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开采与消耗的互相影响。人类开采矿物能源用于冶炼铁矿、铜矿等金属与稀有金属,制造工具与设备;而这些工具又反作用于能源开采,提高开采效率与规模,形成“开采-冶炼-制造-再开采”的闭环,加速了矿物资源的消耗。并且矿物能源还衍生出化纤非金属材料,进一步扩大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范围。

1889年的埃菲尔铁塔
另一方面,化石燃料产生的模式注定了过度依赖它最终会摧毁地球的新陈代谢系统并导致化石能源时代的终结。其原因在于物理学和人类学两个方面:从物理方面看,这些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其次,开采量增加导致开采技术逐渐复杂化,资源消耗速度会远超其再生速度;最后则是系统性的问题——其导致的自然灾害可能阻止人类继续开采。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可能会因为环境原因而思考如何替代化石能源;此外,人类科技进步可能推动生物材料工业的诞生,进而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不难发现,能源转型问题涉及许多学科。哈罗伊教授认为,想要回应这一复杂系统产生的问题,不能再像19世纪那样严守学科壁垒,而应当构建横向的思考模式,才能弥补认识的盲区。这一报告的新颖之处在于自然科学视角的启发性:用能源利用的方式来划分超长时段的人类史。对时段划分的考察角度变为如何固定太阳的能量,如何使用这些能量,并且人类的这些使用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这些涉及物理学的研究视野是传统史学所不具备的。我们同样从讲座中感受到能源转型问题的迫切性:不论是从物理学还是人类学出发,我们当下的能源体系都是不稳定的。然而,在探讨融合了历史与未来的视角的人类纪时,我们仍有一个重要的疑问:当下的人类所处的位置是什么?对于生活在发展较慢地区的人们,他们是否拥有与发达地区居民同等追求能源消费的权利?鉴于人类纪的概念通常基于整体的视角,它可能无意中忽视了个体的具体情况。

9月23日上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米海伊·科尔比埃(Mireille Corbier)教授围绕“罗马帝国世界与水的管理”这一主题做了报告,为与会师生提供了古典时期环境史与资源史的研究视角。科尔比埃教授在其报告中,从四个维度深入探讨了罗马帝国水资源管理的历史脉络,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再到文化层面的渗透。首先她介绍了罗马法中有关水的管理条款,古罗马的法学家强调对水的使用是非垄断性的,如山坡上层建筑的居民无权剥夺下层居民使用淡水和雨水的权利。法律层面的规定彰显了罗马帝国对水资源合理使用的重视。水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它与帝国城市的分布关联上——罗马帝国很多城市沿地中海海岸、大河沿岸或河流港湾而建。除了便于利用水资源的考虑,河流的水运功能对城市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经济和军事意义。我们常常能从史料中发现相关的记载,以莱茵河为例:其航运在帝国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时的运输货物包括羊毛、葡萄酒桶等商品,旨在满足意大利地区的需求。
科尔比埃教授在讲解罗马法之后,详细介绍了罗马城市的供水系统,该系统通常由高架水渠、配水管道和取水装置等部分构成。她强调,通过考古发掘罗马帝国城市遗址,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对城市供水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了解决这些庞大工程的资金难题,除了公共财政的支持,帝国还积极吸引贵族和富人投资参与水管的铺设或取水设施的装饰。一些铭文显示,除了政府鼓励这一原因,这些人的积极参与可能是出于维护个人社会地位的考虑。罗马帝国的管道供水技术十分先进,管道网络在城市地下连接高架水渠、蓄水池与取水点;然而,由于部分水管使用铅材,这可能导致了铅中毒的问题。此外,连接水源与城市的城际高架水渠,采用石灰作为黏合剂,以拱券结构建造,并利用木质支架进行搭建,有效减少了漏水现象,确保了建筑的稳固和正常运作。这些高架水渠遍布整个帝国,从安纳托利亚到毛里塔尼亚,再到阿尔及利亚,伊比利亚半岛的65座水渠中,甚至有一部分直到公元5世纪仍能正常运行。除了基础的用水设施,罗马帝国还拥有其独特的温泉文化。温泉不仅具有健身和清洁的功能,还成为了会议和表演的场所,这既反映了罗马人对温泉的热爱,也揭示了罗马政治生活与公共场合的紧密联系,也解释了为何在罗马帝国衰落后,中世纪的温泉主要作为疗养设施使用,而不再具备之前丰富的文化与体育功能。
科尔比埃教授继续阐述了水资源管理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水力装置。这在古罗马资源史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城市水资源的利用和城际水资源的运输,而对罗马帝国的水力装置关注较少。教授指出,欧洲史学界曾普遍认为罗马帝国主要依赖奴隶劳工提供动力,水车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奴隶数量减少导致的动力短缺。然而,马克·布洛赫在文章中提到,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即2至3世纪,水车装置已在帝国内广泛使用。这一观点得到了1987至1994年法国南部考古发现的证实:除了水力驱动的石块切割装置外,阿尔勒还发现了建于2世纪的水车驱动磨坊。这种驱动装置在当时极为先进,确保了阿尔勒居民的面粉供应。2006年,土耳其学者通过统计,在地图上标注了罗马帝国全境可能存在的水车装置(包括已发掘的和可能存在遗迹但尚未发掘完毕的)。这进一步证实了布洛赫的论断:水车装置在帝国内的应用已相当普遍。除了磨坊,水力资源还被用于灌溉、切割木材和制革业。在满足民生需求的同时,一些水力装置也被用于满足公民或精英阶层的精神需求:斗兽场或圆形剧场会设置水力驱动的抽水装置,以便向舞台区域注水,进行海战表演。作为水的管理的另一面,罗马帝国同样重视洪水防治。教授指出,罗马帝国早已认识到台伯河洪水的威胁,并在流域内建设了众多水利工程以预防洪水对罗马城的破坏;同时,对于那些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干涸的河流,帝国还会定期派遣人员清理河床的淤泥。水能利用与水灾防治是水资源管理的一体两面,帝国各地的水力装置与国家对境内河流的管理,表明古罗马水资源管理能力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
作为结尾,科尔比埃教授将焦点放在了水与罗马人精神生活之间的联系上。在罗马帝国时期,对水资源的重视及其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导致水相关元素频繁地出现在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除了直接描绘河流,水鸟、鳄鱼等动物也常常成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在精英阶层的宅邸装饰中,描绘河流风景的画作同样是一种普遍的选择。除了艺术作品,水与罗马多神教也有关联:许多人会把某条河流与多神信仰中的某一神明对应起来。人们会在河畔修建庙宇,向守护神祈求愿望实现。如果愿望成真,人们就会来神庙敬献祭品。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欧洲基督教化后,为了解决罗马多神教与基督一神教的矛盾,基督教会在河流源头建设神龛,以便信众可以继续保持敬拜河神的传统。科尔比埃教授的报告为国内史学界从资源、经济及精神层面探究古罗马的治理、城市与生活展示了新的可能性。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
9月23日下午,巴黎-西岱大学的马蒂厄·阿尔诺(Marthieu Arnoux)教授围绕“历史性转型与资源系统:工业世界中人类社会的可再生问题”这一主题开展学术报告。该报告主要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视角分析12-18 世纪欧洲铁与煤炭的技术系统演变问题,并探讨人类纪概念下的社会与环境关系。首先,阿尔诺教授介绍了他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他指出,历史学能和其他学科跨学科的合作基础是时间:无论是物理科学、生命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涉及过去,这是一种不可逆的时间,是各个学科所共有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在着眼于未来时往往未能吸取多样化的历史经验,历史学在跨学科合作中的作用便是调动过去的经验,使其作为预测未来的参照系。除了勒华拉杜里与布罗代尔的奠基之作,他还介绍了一些尚未被译出的环境史著作,如理查德·霍夫曼撰写的《中世纪欧洲的环境史》、坎贝拉《大转型:中世纪末期世界的气候、疾病和社会》与让·皮埃尔·德沃里(Jean-Pierre Devroey)的《自然与国王》。
教授强调目前全球变暖的现象迫使各个领域的学者关注环境问题,他将这些研究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气候学家与生态学家的研究,他们试图收集气候系统变化的证据以便对未来气候的变化进行分析和建模;第二种研究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主要关注当今社会既要减轻对气候的影响,又要适应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的必要性;第三类研究历史学家试图探究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类似的能源使用影响气候的事件,而这些环境史的研究建立在历史学家与生态学家的合作基础上,揭示了社会与其生态系统中可观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指出,技术发展并非孤立的领域进步,而是在各个领域形成技术复合体,在不同的技术阶段依赖特定资源、能源使用方式与生产形式;伯特兰·吉勒(Bertrand Gille)则更进一步阐释这一理论,提出所有技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依赖,需保持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贯穿结构、系统、产业链等多个层面,共同构成技术体系。
随后,教授以12至18世纪的欧洲的钢铁与煤炭产业的转型为案例,详细论述了技术体系如何演变。他指出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炼铁主要使用木炭,直到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成功利用焦炭炼铁,他的这一创新使得欧洲人对于能源的依赖逐渐从可再生资源(木材、水力)转向化石能源(煤炭)主导,铁产量不再受限于森林,仅受煤矿储量制约,铁产量因而大大增加,钢铁产业的技术系统革新,为工业革命的展开埋下伏笔。最后,教授还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铁的技术革新发生在欧洲而并非在其它文明?教授认为,这和当时欧洲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与中国将铁匠集中起来进行集中化生产不同,欧洲的铁匠是地方化的,分散在各个村落和城市,因而欧洲铁匠更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用更少的人力来生产更多的金属,因此欧洲中世纪逐渐发展出了高炉炼铁、水力炼铁等技术,这些技术积累终究在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开花结果,在1709年实现了技术突破,开启了以煤炭这样的非可再生资源主导的技术系统转型。
9月24日上午,巴黎-西岱大学的另一名教授彼得罗斯·查齐姆皮罗斯(Pétros Chatzimpiros)进行了题为“在多层次多维度意义上的能源转型与农业养活全球人口的能力研究”的报告。查齐姆皮罗斯教授通过收集1860年起法国农业部和1961年后的各国农业数据,分析了全球农业系统的发展趋势与未来方向,重点探讨了农业与太阳能的关系、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农业全球化,以及当前能源体系下的农业可供养人口这四个问题。教授强调,农业通过光合作用获取太阳能,将其转化为生物能量,用于满足人类食物需求、牲畜饲料需求,同时为社会其他领域提供生物能量。这一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因为农业用地目前已占用全球约40%的无冰土地,而只有当投入农业的能源小于其生产的生物能源时,农业系统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并向其他行业输出能量。
接着,查齐姆皮罗斯教授以法国农业为例,揭示了目前农业的生产以及能源使用情况。他指出,20世纪是农业的转型时期,原本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自然能源和有机肥,生产方式较为传统,而到了20世纪初,技术革新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首先是化学上的革新,1913年的哈伯-博施法让氨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工业氨肥的使用量从此显著上升;其次是农业的机械化革新,20世纪以来,法国农业的拖拉机数量大幅增加,而畜力与农民数量锐减,这些技术革新使得原本法国小农式的生产方式逐步向大规模的企业化生产转变。生产力的提升使得许多国家的农产品出现了盈余,农产品贸易开始全球化,谷物、肉类、油料作物、水果蔬菜、咖啡、可可等农产品在1986-2016年间的贸易量显著激增,全球食物贸易呈现出“少数净出口国供养多数净进口国”的格局。然而食物贸易在运输过程中消耗的燃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目前全球约30%的能源都消耗在农业中。
查齐姆皮罗斯教授认为,当今农业对于能源的消耗不具备可持续性,诸如化肥的使用虽然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但也会导致诸如水体富营养化等农业污染,这都会提高以后农业生产的难度。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150亿,如果要依靠农业供给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要关注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高能源消耗,合理化全球粮食贸易,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与资源错配,更加需要提倡高效有机农业,平衡化肥以及污染较少的有机肥料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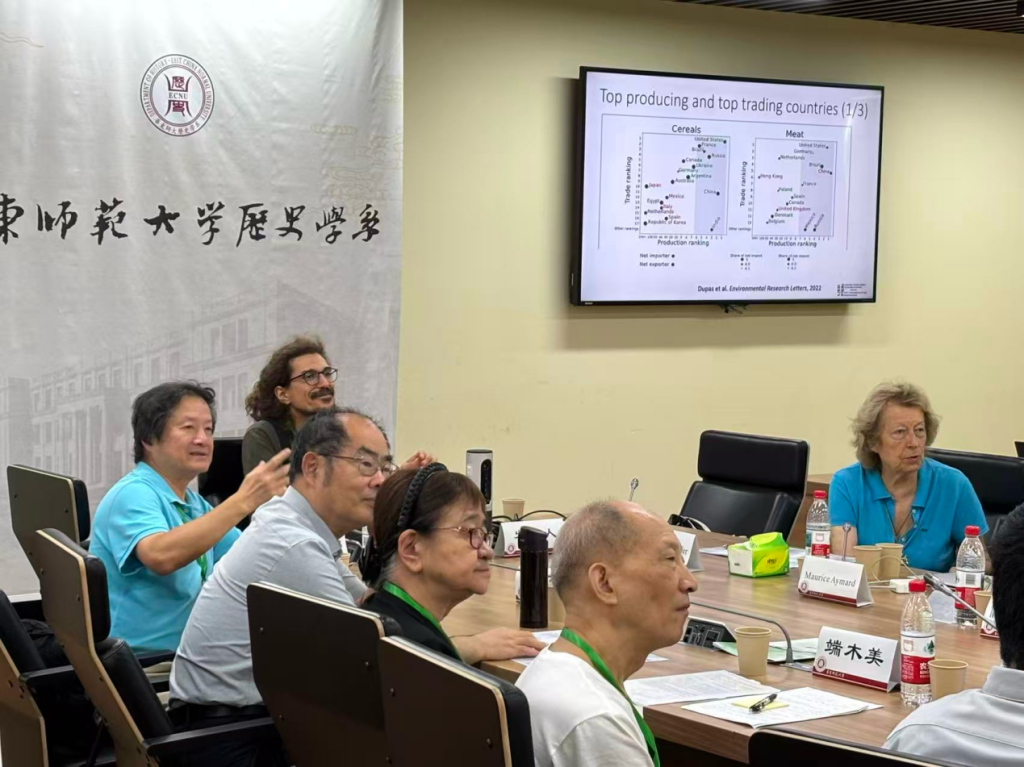
9月25日上午的讲座由日内瓦湖—贝加尔湖欧亚协会创始人菲利普·吉夏尔达兹教授(Philippe Guichardaz)围绕“水资源的历史:人类纪前后的贝加尔湖”这一主题展开。该报告梳理了人类从古至今接触贝加尔湖的历史,综合了贝加尔湖自然、文化和环境保护的多重视角,强调了对其保护和尊重的重要性。在简单介绍贝加尔湖的地理环境之后,吉夏尔达兹教授指出,贝加尔湖与人类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最早与贝加尔湖接触的是被称为布利亚特人的蒙古族裔,他们信奉萨满教,将贝加尔湖视为圣湖,认为其具有强大的灵魂,因而十分尊崇贝加尔湖。教授认为,这些萨满教对于自然的尊崇是如今生态保护学说的雏形,而他们对贝加尔湖的尊崇也作为文化遗产遗留了下来。在第二个阶段,随着17世纪以后俄罗斯殖民者的到来,贝加尔湖周边的主要居民是信奉天主教的俄罗斯人,他们将贝加尔湖视为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吉夏尔达兹教授通过展示这一时期主教、旅行者对贝加尔湖的各类描述,说明贝加尔湖如何以壮丽的山水风光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被赞誉,强调了其应受到绝对尊重与保护的共识。而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苏联成立至今,随 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围绕贝加尔湖的环境保护产生了一系列的争端。尽管苏联时期曾出台法规,旨在保护贝加尔湖的水质与生态,但在1960年,苏联政府还是决定在贝加尔湖旁建立纤维工厂,这引发了科学家们的强烈抗议,但这并没有阻止政府的决策。在这之后,贝加尔湖遭受了工业的严重污染,尽管污染面积仅占流域的0.54%,但破坏巨大且难以修复。1985年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有关贝加尔湖的民间抗议运动得以壮大,但直至2008年,俄罗斯政府才通过强迫工厂采用闭环生产等方式尝试解决污染问题。2013年以后,这一工厂因火灾永久关停并被拆除,尽管生态恢复取得进展,但工人再就业成为新挑战,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

贝加尔湖
目前对于贝加尔湖的保护主要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人类活动,特别是旅游业的过度发展,导致了垃圾堆积和水质污染;其二是气候变暖可能改变贝加尔湖的水温分布,影响其独特的生态平衡。尽管贝加尔湖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应对这些挑战仍需人类采取行动,以保护这一圣湖的生态属性。
本届以“环境史、资源史与人类纪概念”为主题的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在历时四天的深入交流后圆满落幕。中法两国同样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此次中法研讨班无疑为两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提高认识、交流思想、共同思考解决保护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平台。会议不仅延续了中法学术交流的优良传统,更将历史研究的视角有力地投向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生态与环境议题,展现出历史学在应对当前全球性环境挑战中的人文关怀与独特价值。
而就历史研究本身而言,本次研讨班成功跨越了单一学科视野的局限,真正实践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讨班中历史学与生态学、地质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对话表明,面对人类纪这一宏大命题,任何单一的学科视角都是不足的,未来的研究应当更自觉地打破学科壁垒,互相交流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从历史的纵深处寻找资源利用、技术发展与社会形态相互作用的模式与规律,从而为构建一个更具韧性与可持续性的未来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