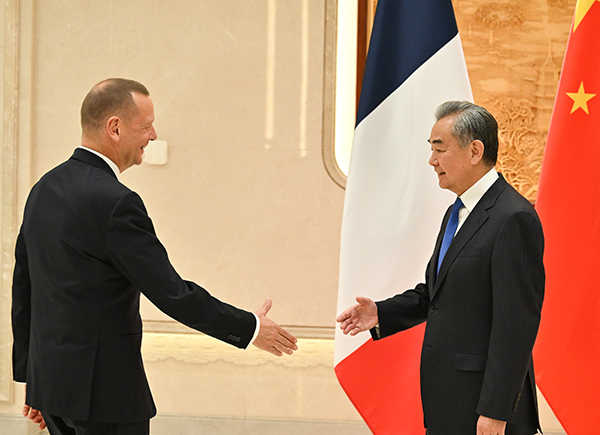9月26日,由米未传媒主导、马东主持的喜剧综艺《喜人奇妙夜第二季》在腾讯视频开播。算起来,这可以算是2021、2022年两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和2024年《喜人奇妙夜》之后,马东和米未传媒旗下的“喜人”(喜剧人的简称)们的第四季节目。节目已经来到第四季,之前三季的冠军喜人团队已经坐上“导师”席位,后继喜人主导的第一期喜剧作品略显疲软,倒是不遵循叙事逻辑、荒诞到有点荒唐的喜剧作品《技能五子棋》成功出圈,在互联网上掀起洗脑之势。相比于过往喜人们的出圈之作,《技能五子棋》毫无疑问是争议最大的,被称作“喜剧香菜”,喜爱的人奉为神作,不接受的人不仅笑不出来,甚至颇感愤怒。

《喜人奇妙夜第二季》
喜剧品味因人而异,但《技能五子棋》的爆火,显然是当今观众喜剧品味变迁的重要标志。实际上,试图改造观众传统喜剧审美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以素描喜剧(sketch)起家,历经三季节目,尽管没有达成将素描喜剧推广为国内喜剧主流的最初目标,但却的确深切地为当代互联网观众的喜剧审美变迁推波助澜。节目和喜人们试图引领风向,但也不排斥寻找和站在风口。
曾经夺冠的蒋龙在《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节目前采时感叹自己“过时了”,激发无数观众眼泪的“某某某”小队如今却争议不断,四士同堂团队以脱口秀、漫才、话剧、解构名著等元素逐步改造了素描喜剧,曾经是“怪人”的“大巴车”上的土豆、吕严,已然成为节目组、喜人们和观众们心中一致的“宗师”,到如今《技能五子棋》的出圈,梳理四年来“喜人”综艺的创作风格与审美变迁,同样也是一部短暂但多变的当代互联网生态与精神演进的历史。
“喜人”大赛 =“素描喜剧”秀?
回到2021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刚刚播出的时候,当时国产综艺领域已然是一个对喜剧小品综艺有所倦怠的时期了——从《欢乐喜剧人》一炮而红的国产喜剧小品综艺,其实一直没有摆脱自己作为春晚小品审美的延伸这一身份。某种意义上,大量开心麻花舞台剧演员加入的小品也依然是传统的春晚小品,尽管增添了话剧质感、表演能力和叙事基底,但审美依旧无法超越春晚模式的既定藩篱。事实也证明,当沈腾、马丽、贾玲、贾冰等一批从喜剧小品综艺走上主流舞台的喜剧演员进入春晚后,并未彻底意义上革新小品的面貌,反而还因为过度煽情、沉迷说教、笑点稀少、品味不符合当代观众等问题,更进一步让小品这门喜剧形式远离了当代观众。很多年轻人爱玩春晚小品“包饺子”的梗,实际上纵观春晚小品四十年历史,只有一个结尾是“包饺子”的作品,而令大众产生这一集体印象的原因,恐怕拜《欢乐喜剧人》所赐;这恐怕也是一种荒诞的“印象反哺”了。
时代和青年人都在寻找和呼唤新的喜剧审美。先发的是李诞和笑果文化对脱口秀——实际上是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综艺化的开拓,而到了2021年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马东和米未传媒找到的抓手,是素描喜剧(sketch),甚至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官方英文名,就是“超级素描喜剧秀”(Super Sketch Show)。
素描喜剧源自美国,从一开始就和综艺节目联系密切,《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简称SNL)甚至是很多国人的外国喜剧启蒙。素描喜剧要求直接刻画并放大、夸张生活,第一时间与网络热梗、社会热点、青年人的精神世界互动,摒弃起承转合的完整戏剧结构,以碎片化的场景和即兴成分较高的表演,将一个既定的喜剧点、冲突点、反差点(“game点”)进行反复强化(“升番”)直至高潮。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之前,上海东方卫视已经有一些将《周六夜现场》引入国内的尝试,素描喜剧对场地、道具需求不高,也使其伴随脱口秀在国内的发展在线下场地逐步铺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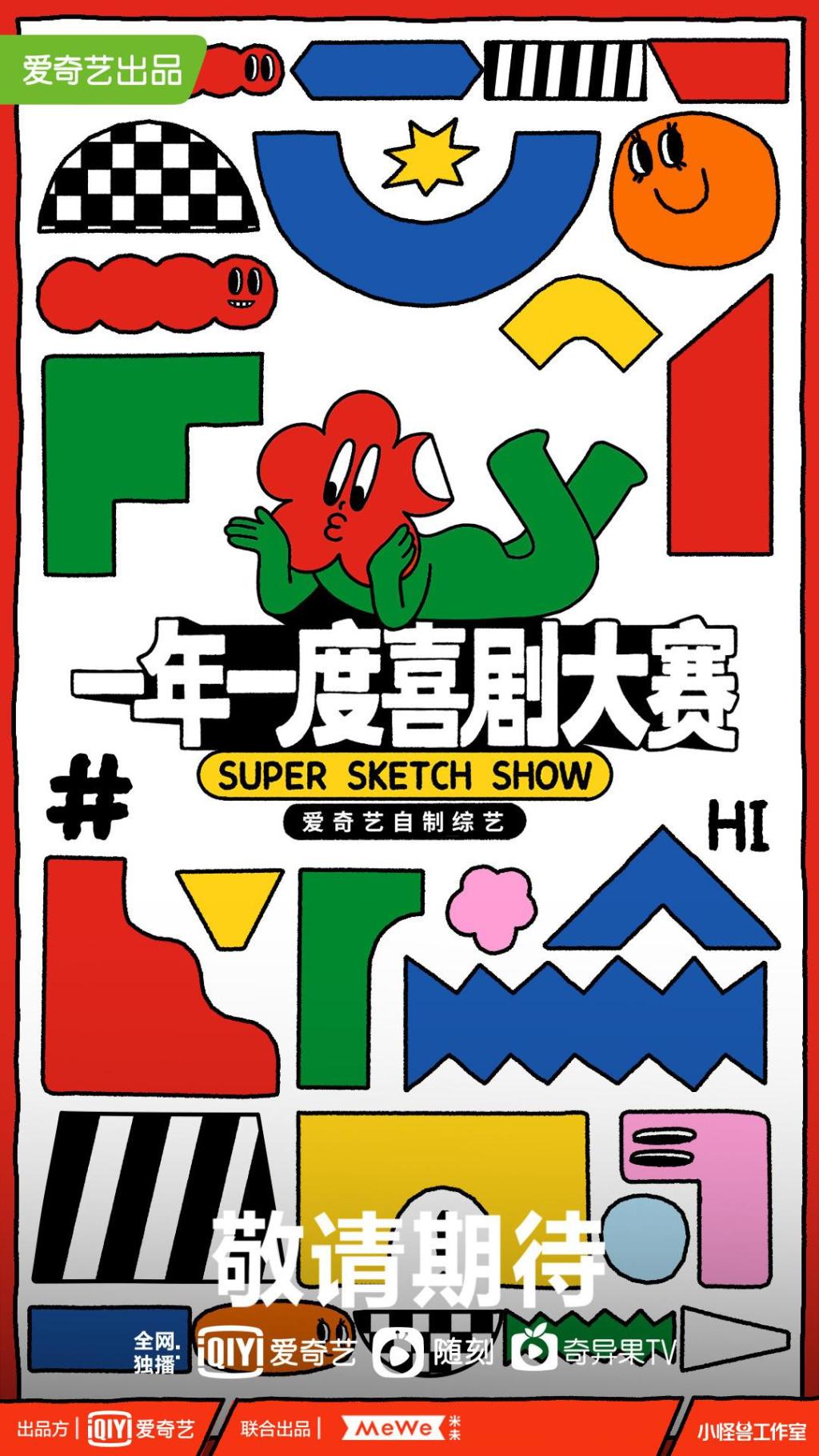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海报
除了素描喜剧,《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还希望将更多形式的新式喜剧纳入节目之中,如默剧、木偶剧、儿童剧、漫才、音乐剧、独角戏、甚至日本综艺中的“超级变变变”形式都被推到前台。节目“求新求变”的主动意识是很强的。后来据一些参与演员回忆,不少传统的、春晚或话剧模式的小品作品哪怕展演的效果很好,也被导演组拿下没有加入节目,导演组希望所有参与的喜剧演员,都按照素描喜剧的模式进行创作,不少演员更是进了米未传媒的“喜剧监狱”后开始现学sketch,从零开始进行创排——《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野心非常明确,就是借助“素描喜剧”为抓手,试图改造国内喜剧审美,创造青年人和互联网更为热衷的喜剧小品形式。
不过,节目最后的发展趋势,显然与节目组最初的设想有些出入。
的确,大多数“喜人”都奉献了他们的sketch作品,《互联网体检》等作品一炮而红,素描喜剧的新鲜感的确第一时间征服了观众。但是,素描喜剧相较于国内观众的“水土不服”也是很明显的:素描喜剧的体量显然是太小了,一个game点对于一个3-5分钟的作品也许是正好的,但到了10分钟、甚至20分钟的国产小品来说,其笑点是容易不足的,观众是容易疲劳的,此时,观众会要求更多单凭素描喜剧结构所不能提供的东西,比如剧情,比如表演,比如人物形象,比如价值观。闫佩伦、张祐维的《一心不二用》就是一个例证,作品是建立在“一心不能二用”的唯一game点基础上的纯粹升番的标准sketch,创意、技术和表演上都无可挑剔,但显然这个game点本身的笑点就不足,更偏滑稽而非“爆笑”,作品又完全没有提供game点之外的其他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作品的“升番”也没有做到递进到高潮,有些沦为重复),因此并未得到观众的普遍喜爱。
这种素描喜剧的水土不服是普遍性的。随着节目的进行,喜人和观众们都逐渐意识到,素描喜剧核心的“game点+升番”结构毫无疑问是开拓、丰富喜剧形式的好点子,但如果只做素描喜剧,是无法在节目里走得长远的。类似《三毛保卫战》《时间都去哪了》《偶像服务生》等作品的出色,毫无疑问是借助了网络热梗,不完全能受到时间考验;江东鸣组合的刘关张三国系列虽然game点始终是“刘备总被关张忽略”,但必须立足于观众对三国故事的熟悉才能够把笑点打坚实。
而被公认为第一季节目最“伟大”的两个作品,《笑吧,皮奥莱维奇!》和《父亲的葬礼》,虽然都有明确的game点和升番结构,一个是“喜剧人却不敢搞笑”,一个是父亲葬礼上一个个出现逐渐离谱的故友,但显然前者是喜剧人的“元喜剧自白”,落在了以欢笑、喜剧和艺术对抗专制强权的价值观上,后者则是把重点放在了漫才吐槽役的独特效果,以及对“升番”概念做出的超出逻辑的解构(包括后来观众对其“父爱”和男性个人成长的意义解读)。这都证明了一个道理:好作品必须有素描喜剧的元素,素描喜剧的结构毫无疑问是一剂拯救喜剧审美的良药和强心针,但单有素描喜剧是不行的,观众显然要得更多。
最有意思的例证,就是第一季的最终冠军“逐梦亚军”组合,蒋龙与张弛。二人都是学院派表演系出身,不仅一身传统小品的历练,更是有戏曲的底子,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最传统的一拨喜剧人,甚至给人一种是来《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现学sketch的观感(纯观感,可能不符合事实)。而从作品也能看出,二人的第一个作品《这个杀手不大冷》是一个纯sketch,game点在于蒋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绑匪,不断依靠二人的声乐能力升番,节目效果很好,但相信观众和他们自己都意识到,节目的出彩其实并不依靠这个单薄的game点,而是依靠了他们出众的音乐表现力。他们的后续作品《女友来了》也是同样的路径,然而就开始收获“除了笑没有其他意义”的质疑。逐梦亚军组合(加上编剧六兽)的才华正在于这种对喜剧的直觉,他们很快开始将自己传统小品表演能力的优势反哺素描喜剧;《最后一课》的game点是优秀表演系毕业生与密室演僵尸之间的反差,但作品添加了完整的故事和人物,上了“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的价值;《台下十年功》更基本是一个传统小品,sketch的结构已经不太明显,张弛的“戏曲梦”成为了节目的煽情大底;最后的《悟空》更是唤起了大众的西游情怀,完成了一个标准的《欢乐喜剧人》式的抒情作品,赢得最终冠军。
事实是,以逐梦亚军为代表的传统喜剧人在借助了sketch结构丰富了自身的喜剧武器库后,对只做素描喜剧的新喜剧人形成了降维优势。可以印证的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的冠军某某某组合,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复制了逐梦亚军的路线,先是以最纯粹的素描喜剧《排练疯云》出发,但很快就开始不断往节目里加入关乎生死的“煽情大底”,最终以感人程度远超好笑程度、煽情但却不让人反感的《再见老张》夺得冠军,击败了一度风头无两,并且努力在一个相同的game点上螺蛳壳里做道场,极尽炫技之能事,并做出具有延续性的长篇系列作品,可以说是纯素描喜剧在三季节目中的最高成就的《少爷与我》系列。
素描喜剧的优势和劣势,在两季节目里暴露无遗:显然,“喜人”们想做“素描喜剧秀”的目标是不成功的,不仅素描喜剧没有一统天下,节目引入的默剧、音乐剧、木偶剧等形式也都没有受到欢迎,看似观众们的喜剧审美只是受到冲击,没有真正被改变,传统春晚小品的力量依旧强大。然而,事实证明,等到了2024年的《喜人奇妙夜》,喜剧确实变了——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只不过不是节目组曾经设想的方向。
“吐槽役”与喜剧结构的极致与衰落
2023年因为各种场外因素,脱口秀和喜人都沉寂下来,2023年成为没有喜剧综艺的一年。在这安静的一年里,互联网生态和观众们的口味得到了沉淀,一个很突出的风向,即是蒋龙在节目中提到的,传统喜剧“过时了”。无论煽情的度把握得多么精妙,无论最终上的价值多么合适、多么激发共鸣,观众们逐渐对喜剧节目必须要有“大底”产生厌倦,“大底”成为一种令人厌倦的喜剧套路,完整的故事结构和惟妙惟肖的人物也不过成为让“大底”显得不太突兀的套路手段。曾经的冠军组合并不再被当作喜人综艺的代表,相反,第一季中途淘汰、第二季也仅仅是第四名的“胖达人”组合土豆、吕严,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喜人新喜剧的代表,被互联网观众们重新考古并反复提及。
严格意义上,这两个人做的也不完全是素描喜剧。吕严的风格非常明显,被公认为中国漫才“第一吐槽役”,无论是否与土豆合作,吕严始终是站在“直人”位置上负责代观众之口进行吐槽,他的发音,节奏与表现力独步天下,表演能力相对短板(只是相对),实际上吕严个人没有做过纯粹的素描喜剧。而土豆的创作风格非常复杂,无法以单纯的风格来定义。《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是标准的漫才,《父亲的葬礼》是漫才+Sketch,《代号大本钟》却又是陈佩斯风格浓重的角色互换传统喜剧,《进化论》则又是game点明确,不断升番,但却又刻画了精彩的“人物”的长篇素描喜剧——这些复杂的定义只能说明一点,即土豆和吕严的喜剧始终是天才般超出观众预期的,既定的结构无法框住他们,因此在逐渐套路化的“喜人”中脱颖而出:观众越来越能猜到其他喜人会做什么,但土豆与吕严,始终每一次都是新的。2025年,他们已然成为所有人口中的“大师”,是新一季节目众望所归的冠军预定。从主流之外的小放光彩到成为主流,土豆和吕严其实并没有改变自己,他们一直在做自己,于是等到了时代和观众的选择。

《进化论》
不过,尽管土豆、吕严的作品每一部都天马行空无法预测,但有一个一直固定的优势点:即吕严作为吐槽役的强力输出。2024年《喜人奇妙夜》播出前后另外一个风潮,则是日本喜剧形式漫才的中国化路线被逐渐走通。从最早李诞带领的各种尝试(实际上,李诞、王建国、庞博、杨笠、杨蒙恩等笑果文化成员的漫才尝试,现在看来也并不糟糕,其反响的平庸还是与漫才早期接受度有关),到肉食动物、徐浩伦与谭湘文等组合的逐渐大众化,哪怕漫才中“怪人”的犯蠢有时候还是无法令观众接受,但“直人”的吐槽已经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风尚了,最早从《银魂》开始的“二次元吐槽”形式逐渐成为了青年文化的显学。
在《喜人奇妙夜》中单飞的吕严,拿出了《小品的世界》这一出圈作品,几乎是“贴脸”式的唤起大众对春晚小品的最终情怀,以决绝、强烈的吐槽役形象,对传统春晚小品做了温情但坚定的告别,打开了新形式吐槽役喜剧的大门。《小品的世界》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最初想达成的目的:离开旧的喜剧,走向新的喜剧。只不过,这个新的喜剧,并非节目组一开始想到的素描喜剧,而是在传统喜剧小品的基础上,在有完整叙事和人物的基础上,加入吐槽役视角的“全民吐槽役”喜剧——《喜人奇妙夜》由此走出了冠军四士同堂,走出了作为编剧和吐槽役的刘旸。
与一般的漫才或者是吐槽役为主的素描喜剧不一样,也与《小品的世界》尽管有强吐槽役,但依旧存在game点和升番结构不同,刘旸的作品的特点在于,首先它类似逐梦亚军的作品一样,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并且擅长借助名著和传统文化底蕴增添情怀,从大的架构上,很难说他的作品是素描喜剧;但是从具体情节的进程中,刘旸会塑造一个又一个单独的,互相独立,各自升番的,但与主线剧情关系并不密切的game点,将作品填充得非常饱满,拿开串联其中的叙事线索,实际上刘旸做的是在一个作品中融合3-5个sketch的“走量”;最后,刘旸个人作为吐槽役,他的吐槽点其实并不会集中在作品的game点和核心矛盾上,与吕严始终在跟着game点吐槽不同,刘旸更多地像写作脱口秀那样,在作品中不断添加文本生成出来的“吐槽梗”,他这个吐槽役实际上是外部的,负责吐槽一些“怪人们”的细枝末节和插科打诨,即吐槽役本人不加入剧情,也不吐槽剧情,纯粹作为观众的视角为作品添加笑点而存在,可以被称作为“吐槽自由人”。
四士同堂创作的基本模式,也就是另外三个“怪人”对付刘旸一个“直人”,无论是《八十一难》中的沙僧还是《越狱的夏天》中的小喇叭二狗,刘旸所扮演的吐槽役角色都是相对被动的,是被其他角色所推动和改变的角色。其主要的存在意义一是串联剧情,二就是作为早观众0.5秒暴露出“怪人们”的吐槽役,为观众始终带来吐槽的快感,而非是漫才或者是吐槽式sketch,把吐槽作为核心——吐槽在这时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习惯,而习惯,是不需要被强调的。
因此,四士同堂这两个最出众的作品,其实最被观众记住的梗也不在刘旸身上。尽管沙僧从头到尾嘴碎一直在吐槽,观众记得的是“隋三藏”这个精妙的文化结构,以及“终一生渡世人,和终一世渡一人,为师觉得是一样的”的上价值;尽管小喇叭二狗最终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异常动人也紧贴《水浒传》内核,但这个节目的最高闪光点毫无疑问是“好汉歌刘欢”出现的一瞬(这也恐怕是三季节目中仅次于《父亲的葬礼》中土星出现之外,素描喜剧风格最为闪耀的瞬间)。而对于刘旸作品最根本的质疑在于,一如刘旸本人争议不小的“卷”的人设,实际上刘旸的作品已然把一种创作模式推到不可延续的极限:故事贴合名著文本做到极致的完整和立意,结构上往一个节目里加入3-5个sketch的game点,文本上做到每一句都有吐槽梗的脱口秀式密度,四士同堂的作品在完美呈现之余,也必然暴露出一种核心的疲惫和创作上的难以持续,换句话说,从他每一句话都要出梗的自我要求就可以看出,这种模式,太累了,对他们自己累,观众也累了。
喜剧的不可持续与返璞归真
此时,2025年《技能五子棋》的出现与爆红,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极繁回到极简的返璞归真,是其他的喜剧结构都已穷尽,只剩下漫才所带来的“吐槽役”,吐槽不仅要成为习惯,更是要重新占据主导的潜意识涌现。如果叙事、结构和人物都被写到极致了,20分钟的时间也很难再攒出什么大活儿了,那么“怪人”莫名其妙,天马行空,无限预期违背的“使相”,这种最为“原始”的搞笑,似乎再次成为观众的期待。相比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时明明非常好笑,却被认为相对“低级”的宋木子与《三狗直播间》,《技能五子棋》其实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狗坨子”,但是多了一个负责吐槽的张呈,也让当代互联网精神状态异常美丽的观众们纯粹的、神经病似的笑点找到了出口,甚至可以说,张兴朝这样的“外星人”,发扬光大了曾经被低估的宋木子们的道路,为三狗“翻了案”。

《技能五子棋》
历经五年四季节目,素描喜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内的喜剧审美,但是却普遍让观众熟稔了喜剧的基本规律,抓到了最为核心也是最简单的“game点+升番”结构,从而把所有人都培养成了潜在的吐槽役。如今的我们看喜剧,面临一种对喜剧形式和结构都了然于心的“知识的诅咒”,我们厌恶故作高深的大底与煽情,觉得按部就班的叙事过于缓慢没有爆点,却又能够一眼看清大多数喜剧的结构和可能的升番——想把历经了喜人综艺的观众们逗笑越来越难了,喜人综艺的变迁史,也就是“吐槽役”逐渐统一观众审美的历史。
有传言说,马东、米未传媒和正在创排的喜人们都觉得,喜剧创作在这个阶段又有些走到头了,本季《喜人奇妙夜》之后,喜剧综艺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综艺节目,或者说商业资本的开发始终是竭泽而渔的,这个时代也是变化极快甚至是速朽的,曾经可以流行几十年的东西,可以在一瞬间过时;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时代的主宰的事物,可能也就只有几年的黄金时代。对于“喜人”们以素描喜剧开创的新喜剧时代,也许一个暂时的终点,对于整体来说,却也是有利的。
于是,回到《技能五子棋》也回到土豆、吕严,我们会意识到,只有这些喜人还能够承载一些我们对喜剧的期待,因为他们是不可控的,他们是天外来客,他们是“外星从”,他们时刻能给我们带来超出想象的,超出预期的,甚至对现在的人类来说有点为时过早的东西,也反映了当代互联网一代人的内心普遍的声音:
我们什么都见过了,我们什么都能吐槽——除非,还有谁能拿出我们没想到,也想不到的东西吗?比如“土星,你来了”,比如“好汉歌刘欢”,比如“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