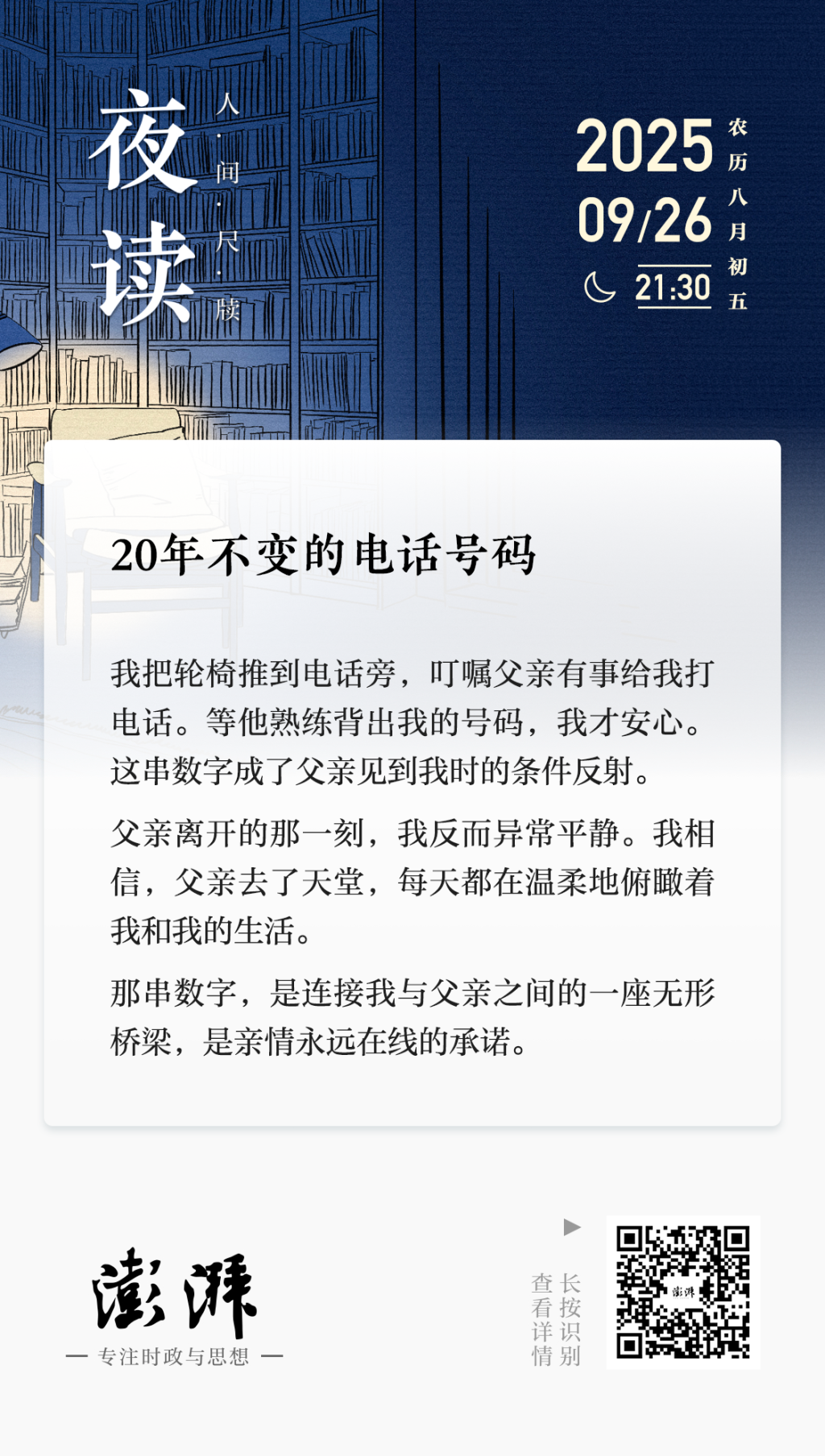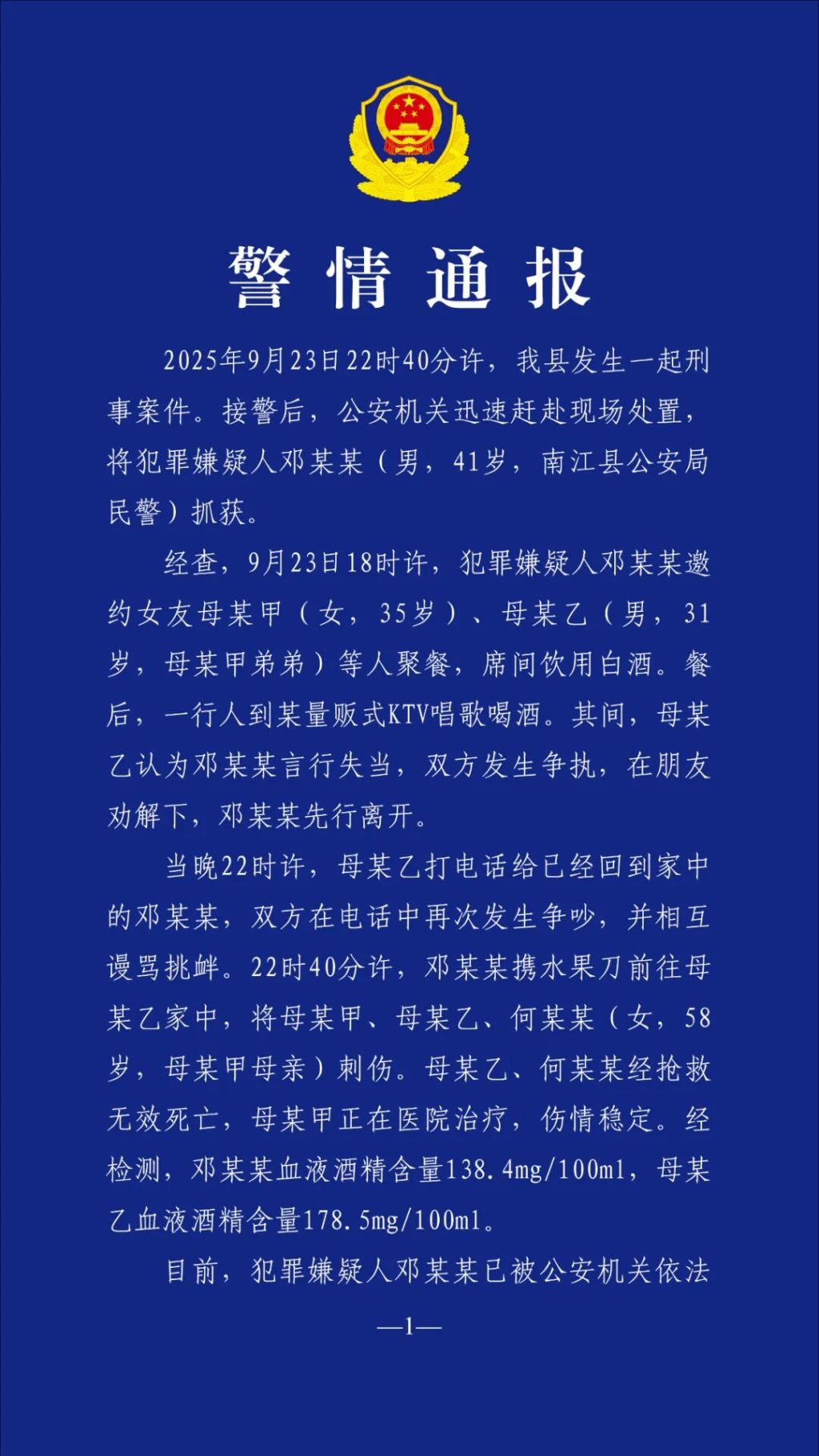2005年一年,我们全家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父亲病了。起初病情并不严重,我天真地以为输几天液,父亲就会康复,重新变回那个爱扫地的快乐老头。然而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脑梗、血尿、行动不便。我和母亲频繁辗转于全市各家医院,办住院手续对我来说已经轻车熟路。
情况稍好时,我们也会回家治疗。有时母亲需要外出处理琐事,我也得去单位办事,留父亲一人在家实在不放心。我把父亲的轮椅推到电话机旁,千叮万嘱有事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每次都要等他熟练地、一字不差地背出我的号码,我才安心离开。久而久之,这串数字成了父亲见到我时的条件反射,仿佛只有准确背出这串数字,才能让所有人都安心。
后来,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一个月后,一纸“膀胱癌”的诊断书,彻底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平静。
我不敢哭,只是呆呆地站着,脑子里嗡嗡作响,一片空白。随后,恐惧排山倒海般压下来,重重地砸在心头。转过身,我看见母亲早已泪流满面。她说话的声音颤抖而无力,我仿佛看到一座高楼的坍塌。
父亲已经失去手术机会,开始了漫长的放射治疗。我日夜守候在他身边。他总是不忍耽误我的工作,轻声说:“你去上班吧,有事我给你打电话。”说完,又熟练地背起我的电话号码。
我请了长假,舍不得离开父亲半步,期盼着奇迹的出现。父亲的精神越来越差,偶尔睁开眼,见到我会露出微笑,会推我走,会无意识地背诵那串熟悉的号码……他日渐消瘦,面色蜡黄,皮肤失去光泽。一顿饭只能吃下半个蛋黄,便摆摆手,再也咽不下去。在病魔面前,我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消瘦下去,看着他在痛苦中挣扎,像个溺水的人,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甚至不敢轻易触碰父亲,不知道把手放在哪个位置能让他舒服一点,也不知道该如何动作才能更好地照料他。我能做的,只有疯狂地寻找医生和止不住地流泪。
父亲难得有不疼痛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对我们而言如同过节。我推着他到外面晒太阳,甚至推他到不远处的顺德市场逛逛,他的嘴角会泛起淡淡的笑意。
父亲真正离开的那一刻,我反而异常平静。我相信,父亲终于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去了天堂。从此,他每天都在高处,温柔地俯瞰着我和我的生活。
阳光洒在脸上,极像父亲的目光。送葬的队伍蜿蜒在家乡的土地上。秋收刚过,几株玉米秸孤零零地伫立在田野里,我孤零零地望着玉米秸怀抱的坟茔。我知道,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那个人,永远地离开了。
如今20年过去了,我通讯录里的人来了又走,唯独这个号码始终没变。很多人劝我换成更便宜的套餐号码,我都笑着摇头。因为,我担心父亲在有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我。
那串数字,于我而言,早已不是简单的通讯编码,而是刻在心底深处的亲情密码,是连接我与父亲之间的一座无形桥梁,是亲情永远在线的承诺。
有些牵挂是可以穿越生死的,就像这串20年不曾更改的电话号码。虽然再也听不到那头的声音,但我想,爱是从来不需要信号的——它早已成为血脉里的奔流,是无声却永恒的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