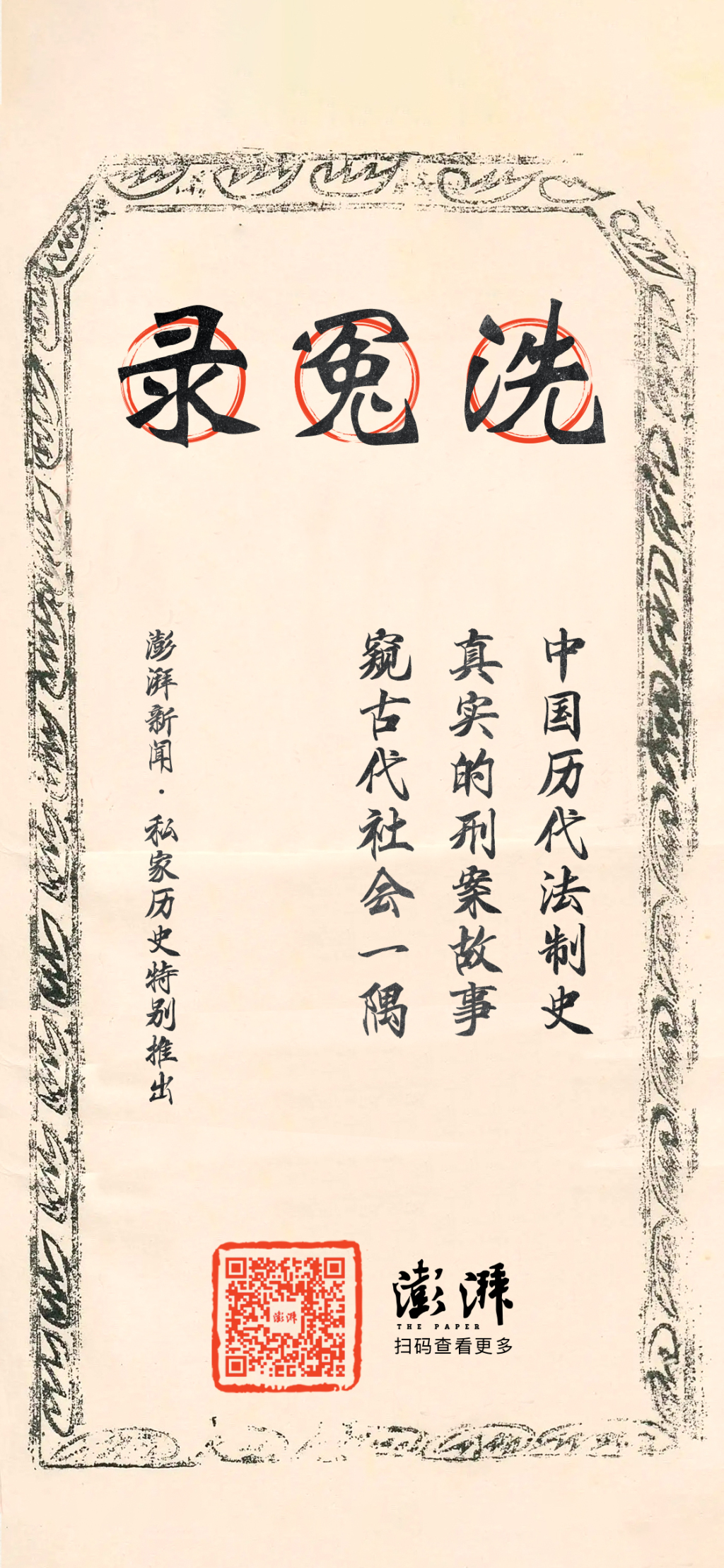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
毒杀格格
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諴亲王允祕面见乾隆帝,呈上一封书信。信是允祕的女儿“七格格”(以下简称为“格格”)寄来的,内容大概是说有人意图毒杀自己,请父亲为自己做主。
乾隆帝读过信后,感觉事情蹊跷。原本,蒙古土默特部在清初分为东西两支,东土默特部(游牧于今辽宁省朝阳县一带)归顺清廷后一直没能与清皇室联姻。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便把叔父允祕嫡出的七格格封为郡主,指婚给东土默特部贝子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的次子纳逊特古斯为妻。二人成婚至今已经有十一年,似乎没有听说他们关系破裂的事情。其次,清代蒙古各部有“年班”的制度,即每隔数年需入京朝觐一次。乾隆三十五年恰逢纳逊特古斯年班,他此时正在京城。乾隆帝由此推测,可能是纳逊特古斯家的奴仆想要毒杀格格,也就是典型的“奴杀主”案件。于是,乾隆帝一面仍令纳逊特古斯照常参加元旦的外藩筵宴,一面派出户部侍郎索琳、署理刑部侍郎的副都统博清额二人,由兼任理藩院额外侍郎的敖汉部镇国公罗布藏锡喇布带领(敖汉部与东土默特部相邻),前往东土默特部调查此案。

东土默特部
索琳一行抵达后即展开调查,得知事情的大概经过为: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格格起床后正在屋里梳头,格格孩子的奶妈赛哈赖拿着一盘饽饽(荞麦面皮猪肉馅儿,类似肉包子)进屋来,朝格格单膝跪下,说这饽饽是进献给格格享用的。格格看了一眼,让赛哈赖把饽饽放在炕桌上,便让她出去了。梳完头后,格格想尝尝饽饽,拿了一个掰开来,闻到有葱蒜的臭味,不想吃,于是就赏给屋里的五个丫鬟吃。五个丫鬟接过饽饽,朝格格磕头谢了恩,就分着把饽饽吃完了。到了中午,五个丫鬟都觉得肚子疼、浑身发麻、昏昏欲睡,先后晕死过去。格格见状,赶紧把纳逊特古斯家里的男管家积兰泰叫进来,问他怎么办。积兰泰观察了一下,发现五个丫鬟的指甲都黑了,应该是中了毒,于是用阿鲁拉(一种蒙古草药)和酸奶混在一起给她们灌下去。过了一段时间,五个丫鬟里的四个渐渐苏醒,只有一个叫赛罕寨的丫鬟没有醒来,一直昏睡,后来在十二月初二日咽了气。格格听说五个丫鬟都是中了毒,就猜到是赛哈赖送的饽饽有问题,派人把赛哈赖关起来审问,赛哈赖并未认罪。
或许是索琳一行觉得这个案子属于纳逊特古斯家的私事,抑或是为了尊重蒙古部长的“主人”身份,他们并没有直接审讯犯人,而是请纳逊特古斯的父亲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代为审讯。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先审讯了赛哈赖,赛哈赖一开始拒不认罪,后来供称,是因为自己不满意丈夫色旺扎布无能,就和一个外人通奸,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想毒死丈夫,但是不小心毒错了人,把有毒的饽饽进献给了格格。至于毒药,则是管家积兰泰给自己的。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又审讯积兰泰,积兰泰供称,毒药是自己去南山采药时候采到的,后来给了赛哈赖,也不知道她拿去做什么用了。
此时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已身患重病,精力不济,审讯本就潦草,而且,积兰泰是他的小舅子,颇受偏袒,没有深究其责任。至于纳逊特古斯,他在索琳等人到东土默特部之前就已从京城返回,由于案发时他正在京师,赛哈赖等人的口供又都没有涉及他,就没有审讯他。如此,在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的审理下,此案被认为是由于赛哈赖失误所致,也并无故意谋杀格格的确证。这样荒唐离谱的结论,竟然得到索琳等人的认可。他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将赛哈赖和积兰泰交给纳逊特古斯,令其看管起来,便收拾行囊启程回京,并将案情奏报给乾隆帝。
乾隆三十六年(1771)正月二十六日,乾隆帝收到索琳等人的奏报,览看之下,大为光火。他认为,即便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和纳逊特古斯没有参与此案,但下毒的赛哈赖是纳逊特古斯的奴仆,父子二人都属于被告之列,怎么能反而让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代为审理,还把赛哈赖等人交纳逊特古斯看管呢?而且,既然未能审明事情,就应该将犯人押解进京,怎么能把他们都留在本地,方便他们串供呢?于是,乾隆帝下旨痛斥索琳等人办案糊涂,要求他们立刻返回东土默特部,一方面护送格格及其子女回京,一方面将所有涉案人等及纳逊特古斯均押解进京。二十七日,已经行抵三河县的索琳和博清额接到旨意,惶恐之下,当日即折返东土默特部,在二月初六日抵达。博清额在初八日护送格格等人启程,索琳在初九日解带纳逊特古斯等人启程,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更是在惊惧之中病亡。
京审之下的实情
二月二十一日,犯案人等均被送至京师,当时乾隆帝已经启程巡幸山东,留下大学士尹继善领衔,会同刑部审理此案。尹继善等官员在当日便组织审讯,严审之下,首先翻供的是赛哈赖。据赛哈赖说,格格性格不好,很自以为是,看不起纳逊特古斯家里上下人等,所以奴仆们都恨格格。纳逊特古斯跟格格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两人都声称身体不好,已经分居三四年了,格格住在里院的正房(北房),纳逊特古斯则住在外院的厢房。而且,纳逊特古斯身边都改让小厮伺候,格格更是对此不满。按照制度,乾隆三十六年是格格例应回京省亲的年份,格格便放出话去,说自己下嫁到东土默特部,却被这样轻视,等自己回京一定向父亲和皇帝告状,让他们给自己做主。赛哈赖害怕皇帝会责罚东土默特部,于是就谋划把格格毒死。
赛哈赖的供词前言不搭后语,又缺乏逻辑关系,难以让尹继善等官员信服。而赛哈赖之前的口供中提到纳逊特古斯家后山庙里有个名叫巴尔丹格隆的喇嘛,此人经常给纳逊特古斯和格格治病。虽然赛哈赖只是略微提到他,但言词颇为闪烁,引起了尹继善等官员的注意,于是接下来,巴尔丹格隆也接受了审讯。巴尔丹格隆供称,自己原本是赛哈赖的家奴,后来出家当了喇嘛。因为自己有些医药知识,经常去给纳逊特古斯家里的人看病,跟格格也熟悉。赛哈赖和自己通奸已经一年多,她给格格下毒,毒药就是自己给她的。巴尔丹格隆的供词明显与之前赛哈赖和积兰泰的第一次供词矛盾,尹继善等官员便重新审讯三人,并让他们互相对质,终于得出实情。
原来,乾隆三十五年夏季,纳逊特古斯准备进京之前,曾将积兰泰、赛哈赖、巴尔丹格隆三人叫到屋里。前文已述,积兰泰是纳逊特古斯的舅父、家里的管家,赛哈赖是纳逊特古斯儿子的乳母,巴尔丹格隆是赛哈赖的姘头。纳逊特古斯对他们说,自己和格格积怨已深,明年格格即将进京,为防格格向她父亲和皇帝告状,不如把她毒死,就在自己进京后下手。于是纳逊特古斯让巴尔丹格隆配制毒药,交给积兰泰和赛哈赖去下毒。巴尔丹格隆知道巴豆和川乌可以治病,但都有大毒,所以用一撮巴豆和四个川乌混在一起,磨成沫子,交给积兰泰。积兰泰是男管家,一般不能进里院,于是把毒药给了赛哈赖,赛哈赖就把毒药下在饽饽里进献给格格。本来赛哈赖还想把毒饽饽给格格的子女吃,但格格的子女都住在里院西厢房,并且当时格格的女儿生病要忌门(满蒙的一种习俗,不能让他人进屋,类似隔离养病),所以没能得逞。后来丫鬟们吃饽饽中了毒,格格叫积兰泰进里院去。积兰泰见状,知道是赛哈赖毒错了人,救治完丫鬟们从里院出来就埋怨赛哈赖。不久,纳逊特古斯回到东土默特部,嘱咐积兰泰三人,钦差大臣即日将到,让他们想办法搪塞过去,因此三人都对钦差撒了谎。
事情查明之后,尹继善等官员急忙奏报给乾隆帝。乾隆帝览奏后,认为这是一件“奇事”。乾隆帝钦定案件时,经常喜欢探究案件背后的人际关系、环境状态,类似今天的“作案动机”。因此,他提出了自己关心的几个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两点:第一,格格身边一共有五个丫鬟,这五个丫鬟里,据说只有一个名叫桂格的丫鬟是从京师王府派去的,其他丫鬟都是纳逊特古斯家的奴仆。按说格格作为亲王的女儿,一定有很多陪嫁丫鬟,怎么只剩了一个桂格呢?第二,口供都说纳逊特古斯和格格不合,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不合的?只是关系不好,就非要毒杀格格不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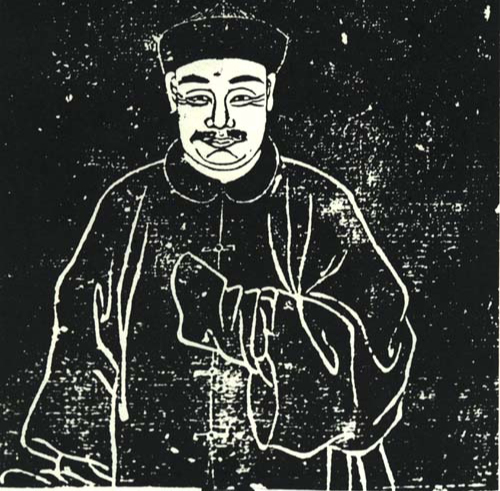
尹继善
尹继善等官员接到乾隆帝的询问,就此追问纳逊特古斯和格格,大概得出以下信息:纳逊特古斯和格格成亲之后,一开始关系还算和睦,先后生下一子一女,但是二人的性格都存在问题。纳逊特古斯放荡不羁,性喜游荡,天天饮酒作乐。格格任性乖张,说话放肆,自恃郡主身份,看不起纳逊特古斯一家人,不孝敬公婆,也不侍奉丈夫。纳逊特古斯便和格格逐渐疏远,想要休妻,却忌惮格格的皇室身份,只能勉强维持。四年前,纳逊特古斯到京城,在庆乐园看戏时认识了大成班唱小旦的戏子添宝。纳逊特古斯很喜欢添宝,就与他结识,还曾让他去自己的住处,赏给他银子、荷包等物品。后来纳逊特古斯回东土默特部,就带了添宝一起回去。有一天,纳逊特古斯看添宝戴着一个金镯子,就把自己手边的金镯子赏给他,让他配成一对。而纳逊特古斯这个金镯子原是格格的,格格知道后就与纳逊特古斯吵闹。第二天,纳逊特古斯将金镯子拿了回来,但他和格格的关系也正式破裂,自己搬到外院居住。
此后,纳逊特古斯偶尔进内院,到正房跟格格说话,但只是随便说几句话就离开,二人的关系十分冷淡。格格当年下嫁的时候陪嫁有六个丫鬟、三个太监、两个老妈妈。后来六个丫鬟年纪都大了,嫁了当地的蒙古人。格格原本想着,丫鬟们就算结婚了也可以来侍奉,后来才知道蒙古人散居各处,各自相距颇远,不可能再进府当差。三个太监病死一个,回京两个。目前身边的娘家奴仆只有一个新派来的丫鬟桂格、一个新派来的太监,还有两个负责带孩子的老妈妈。格格还嫌弃桂格蠢笨,不让她贴身伺候,而让她去伺候自己的子女。只不过案发时格格子女屋里正好忌门,桂格才在格格身边。由于纳逊特古斯和格格关系破裂,格格身边又没有得力的娘家奴仆,因此纳逊特古斯家里的奴仆也对格格很不好,每天送进来的饭菜都很一般,甚至有的难以下咽,连管家积兰泰也总是拒绝给格格她想要的东西。格格原本每年有一百五十两银子的俸禄,但这些钱都被纳逊特古斯领来后拿去花天酒地了,格格每年只有京钱三百三十吊作为全年的开销,过得十分拮据。另一方面,纳逊特古斯对格格不好是事实,但格格也比较浮躁,天天对奴仆说自己要回京告状报复他们,这也加剧了纳逊特古斯和府内奴仆的杀意。
三月初四日,尹继善等官员为此案拟定罪名,他们主要依据《大清律例》里的三条,第一是“用毒药杀人者斩监候”。第二条是“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已行(不问已伤、未伤)者,(预谋之子孙,不分首、从)皆斩;已杀者,凌迟处死”。“若奴婢及雇工人谋杀家长……罪与子孙同。”第三条是“夫故杀妻绞监候”。这三条其实都跟当时的法律秩序有关。清代法律强调血缘和身份的高低,家庭成员需要区分尊卑长幼,服役人员需要划清主仆之分。在此背景下,“尊”或“主”冒犯“卑”或“奴”可以减轻罪责,反之,“卑”或“奴”冒犯“尊”或“主”则需要加重罪责。此案中,夫尊妻卑,因此夫杀妻即便是故意谋杀,也要比一般的谋杀降一等,而奴婢杀主人则要加重。
尹继善等官员认为,纳逊特古斯和积兰泰等人谋杀格格,虽然毒错了人,只毒死了丫鬟赛罕寨,但他们本身是想毒死格格,那么无论结果如何,判决是一样的。因此拟定,纳逊特古斯受皇帝指婚,却行此阴险狠毒之事,大为悖恩,应斩立决;积兰泰、赛哈赖、巴尔丹格隆是纳逊特古斯的部民和奴仆,格格是纳逊特古斯的嫡妻,自然就是他们的主母,奴仆谋杀主母应凌迟处死;赛哈赖的丈夫色旺扎布事先没有发现逆谋,但他的女儿曾告诉他赛哈赖往饽饽里放了某种药物,他却没有在意,因此也有罪,应发配到伊犁给披甲人为奴;另外,戏子添宝竟然敢勾引蒙古额驸,也应发配到伊犁给披甲人为奴。
牵连案件的浮现与结局
然而,尹继善等官员将拟定罪名上报后,却得到乾隆帝意想不到的批复。原来,前次询问作案动机之后不久,乾隆帝正好召见了色布腾巴勒珠尔和扎拉丰阿。色布腾巴勒珠尔是蒙古科尔沁部的亲王,也是乾隆帝的女婿,扎拉丰阿则是蒙古喀喇沁部的贝子。乾隆帝和他们谈到这个案子,色、扎二人对乾隆帝说,去年秋季,纳逊特古斯跟他的亲哥哥吹扎布一起进京,后来吹扎布突然患上重病,奏报上来,因此没有参加年节朝觐就提前回东土默特部了。当时蒙古王公群体内流传一种说法,就是纳逊特古斯给吹扎布下了毒,差点将吹扎布毒死。现在听到这个案子,觉出两件事情可能有所关联。乾隆帝听闻,立即降旨给尹继善,让他彻查此事。
于是,尹继善等官员又开始审理纳逊特古斯毒害吹扎布一案,最后在三月二十三日审完。案件的大致情况是:纳逊特古斯性喜游荡,哥哥吹扎布经常管教他,并请父亲责打他,所以纳逊特古斯便记恨在心。乾隆三十五年六月,二人一起上京前,纳逊特古斯提前让巴尔丹格隆配制毒药,然后在京城时,让管理厨房的侍卫敏集特多尔济下毒。八月初八日吹扎布中毒,浑身发热,连小便都是黑色的,在京师未能治好,只能奏明朝廷后提前返回东土默特部,后来被当地一个叫博巴特的喇嘛治好了。吹扎布身边的人都觉得是纳逊特古斯下的毒,但吹扎布觉得这是家丑,自己又没被毒死,所以没有声张出去,也没有追究纳逊特古斯。
前面讲过,清代法律的定罪会参考人物的尊卑关系,纳逊特古斯毒杀格格是夫杀妻,夫尊妻卑,属于以尊长欺压卑弱,只能判绞监候之罪。而吹扎布是纳逊特古斯的胞兄,兄尊弟卑,纳逊特古斯谋杀吹扎布就是以卑弱欺压尊长,属于悖伦大罪。根据《大清律例》,谋杀期亲尊长,“已行(不问已伤、未伤)者,(预谋之子孙,不分首、从)皆斩;已杀者,凌迟处死”。4尹继善等官员认为纳逊特古斯已经下毒,吹扎布也确实中毒,只不过没能毒死,应按照“已杀”定拟,故应凌迟处死。
实际上,纳逊特古斯毒害格格和吹扎布两个案件,都与袭爵有关。一方面,纳逊特古斯是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的次子,当时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图病重,吹扎布是理论上的第一继承人。纳逊特古斯将吹扎布毒死,自己作为次子,大概率就可以承袭爵位。另一方面,纳逊特古斯对格格不好,若格格进京向宫中告状,朝廷责怪下来,也不利于自己袭爵,遂一并毒死。最终,乾隆帝判决,纳逊特古斯加恩免于凌迟处死,改为斩立决;积兰泰、赛哈赖、巴尔丹格隆凌迟处死;色旺扎布、添宝发配伊犁给披甲人为奴;敏集特多尔济已经逃跑,待抓捕归案后也凌迟处死。
至于格格,乾隆帝对她也持批评态度。此案结案一个月后,乾隆帝下旨给允祕说,如果格格恪守妇道,孝顺公婆,顺从丈夫,那么就不会和纳逊特古斯结仇,纳逊特古斯自然也就不会毒杀格格。从这个角度来说,格格也是有过错的。因此,乾隆帝认为,格格原本应得的俸禄和官方待遇应全部停止发放,只保留郡主的空衔,格格本人和她的子女一起交给允祕抚养。旨意中还专门指出,纳逊特古斯作为败坏伦理之人,他的儿子成年后也不能再封为台吉,只能编入允祕所领有的蒙古佐领之下作为另户旗人,而非蒙古盟旗之人。不过,五年之后,格格的儿子成年,乾隆帝违背了之前的旨意,还是赏给了他二等台吉的虚衔。后来格格就在京师度过余生,她的后代也留在了京师。
案件背后的政治与社会
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乾隆帝的态度尤其引人注意。一开始的索琳等人,或许的确有息事宁人的想法,查办此案颇为草率,妄图含糊结案,乾隆帝则严加训诫,多次强调“人命至重”“岂可使案情介于疑似”。无论乾隆帝此举是否旨在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都同时表达了他秉公无私的法治思维。然而,乾隆帝最早怀疑是奴仆想要谋杀格格,之后证据逐渐指向纳逊特古斯,他仍旧意图为纳逊特古斯开脱,认为可能是办案人员照顾格格的颜面而故意栽赃纳逊特古斯。即便最后证据确凿,纳逊特古斯已经认罪,他仍旧不愿意让纳逊特古斯以谋杀格格的罪名定罪,而是更愿意以谋杀胞兄的罪名来处分纳逊特古斯。乾隆帝的这一态度,其实是典型的政治思维。清代蒙古各部属于外藩,而满蒙联姻更属国策,作为清廷的统治者,乾隆帝认为,如果自己过于强调纳逊特古斯谋杀格格的行为,可能会落下偏袒皇室格格的恶评,致使蒙古各部人心不服。而纳逊特古斯谋杀胞兄一事完全与清廷无关,清廷不过秉公办理,处分纳逊特古斯更加名正言顺,蒙古各部亦当心服口服。

乾隆帝
通过纳逊特古斯谋杀郡主案,不仅可以了解案件本身的审理过程、乾隆帝的处理态度,还可以了解纳逊特古斯和格格具体的生活细节,从而观察当时的社会风俗,认识满蒙联姻这一清代国策的另一侧面。其中颇可玩味的有两点。第一,清代贵族女性出嫁,除陪嫁财物外,大多还要陪嫁奴仆。这些奴仆作为女性从娘家带来之人,是女性的“自己人”,在生活中尤其重要。纳逊特古斯敢于谋害格格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看格格从娘家带来的奴仆已经数量不多,且老少不堪。第二,在外人的想象中,皇室格格下嫁,本身就代表了宫廷的权威,一定会得到宫廷的支持,难免在丈夫家作威作福。本案中的格格也的确在纳逊特古斯家颇为任性,即便是案发之后,她还堂而皇之地对尹继善等官员说:“我是亲王的女儿,让我给纳逊特古斯端茶倒水,我是做不来这种事的!”然而,乾隆帝跟尹继善讨论案情的时候曾专门强调,“格格与纳逊特古斯不和睦,允祕应该早就知道了。就算格格之后进京当面哭诉,允祕又能把纳逊特古斯怎么样呢?”言下之意,无论是允祕还是乾隆帝,恐怕都不会过度偏向格格,只因生活上的矛盾就责罚或降罪于额驸。总之,这件罕见的蒙古额驸毒杀郡主案,可以让今人更好地了解清代满蒙联姻政策下满蒙贵族的生活状态。
(原文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