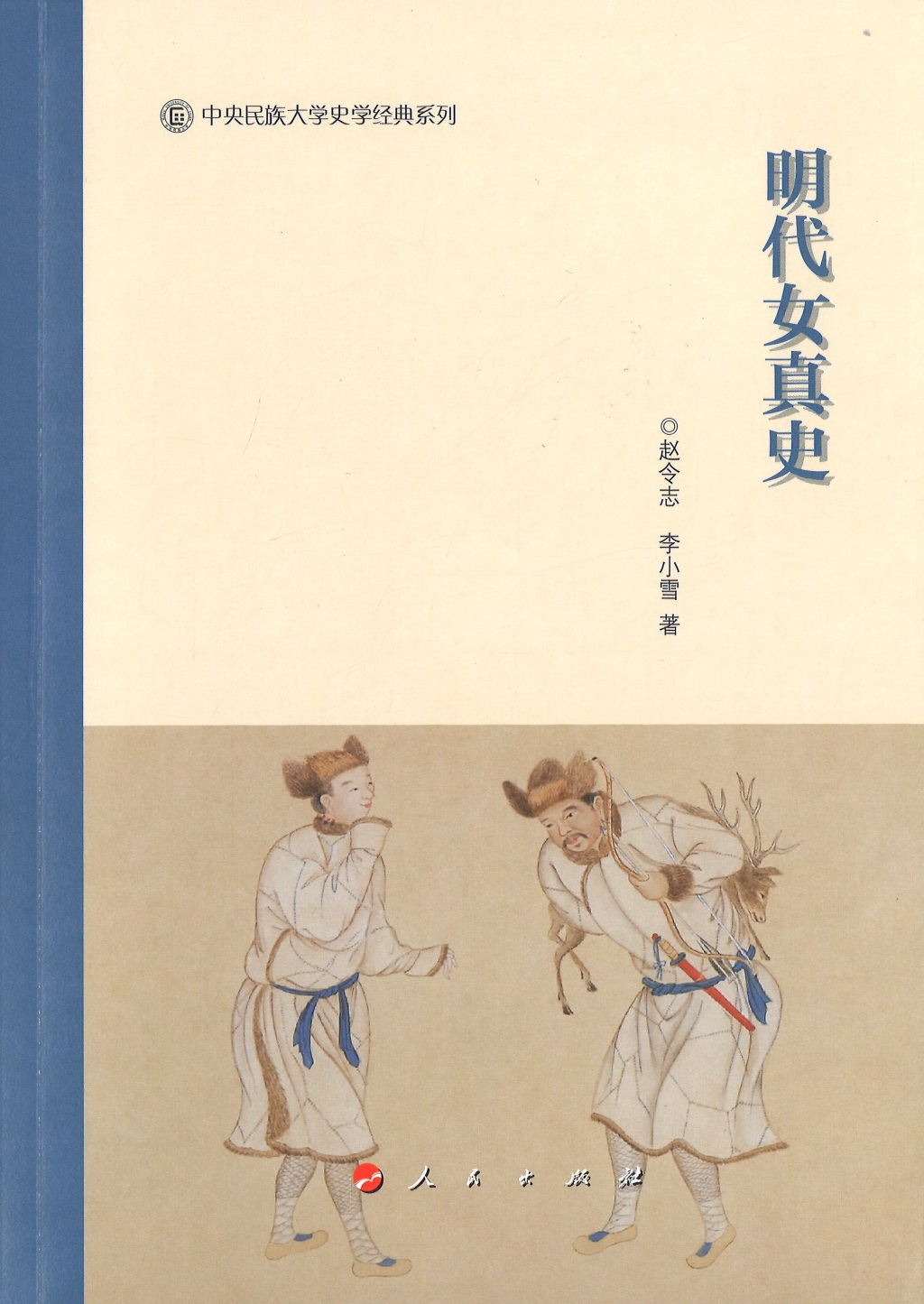
《明代女真史》,赵令志、李小雪著,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490页,60.00元
满族发祥于我国东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先民从周代的肃慎、战国秦汉时期的挹娄、魏晋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辽金乃至元代的女真,均在各代正史中有所记载,且有大量文物古迹作为研究佐证。至于明代女真的史料,无论是《明实录》《明史》等官修史料,还是笔记、游记等诸多私人著述,数量庞大,分布零散,故研究明代女真史的研究论著虽为数众多,但论题却较为分散,难成系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令志教授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民族学学院李小雪老师合著的《明代女真史》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缺。该书从族源考证、周边影响、卫所南迁、统一聚合、建立金国、奠定大清及文化习俗、姓氏特点等方面入手,以现代民族历史研究的新视角,结合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理论视角,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明代女真人的发展历史,以揭示明代女真人何以崛起并在更改族称后很快入主中原的历史变局中的因果关系。
三方势力下的明代女真人
该书与以往的女真史论著的编纂义例和思路有所不同。作者对“女真人”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将辽金时期以前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定义为“女真的先民”,认为女真先民的发展过程,就是南迁的过程,其间虽建立了勿吉国、渤海国、金朝等政权,但这些政权消亡后,南迁的女真人基本融入渤海人、契丹人、汉人等族群之中,与后来兴起的明代女真基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渔猎文化的民族承传关系。而元代生活于白山黑水之间那些留在故地的女真人,与明代女真人存在血缘关系,故元明时期的女真人方可称为“女真人的先世”,与明代女真人及满洲人不但有文化传承关系,亦有血缘关系。
作者特别探讨了明代前中期女真人与明朝、朝鲜、蒙古的关系,认为明代之女真人被明朝招抚并设置羁縻卫所管辖后,亦有部分南迁者。其南迁之后,建州及部分海西女真之生活区域,位于明朝、朝鲜、蒙古之间,三者之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均强于女真人,故凭借各自之实力,分别向女真地区扩张,女真人为自保不得不游离于三者之间,故三者在明代均对女真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影响巨大。当然,三者之中,对女真影响较大者为明朝。自明初招抚女真人,对前来归附者授予敕书、印信,在女真地区设置羁縻卫所后,女真地区逐渐纳入明朝统治之下,担任卫所官员的女真头领,便成明朝之职官。其虽无俸饷之制,然允其定期朝贡、贸易,对女真各部发展实属至关重要,此亦成为明朝掌控女真社会之重要手段。朝鲜虽为明朝属国,但因其属汉文化系列,非系夷狄,故较女真更亲近于明朝。朝鲜利用相同的文化因素,各方面咸自小于明朝,从而使其赢得明朝皇帝信赖,成功将女真人排挤出朝鲜半岛北部,将元以前之铁岭边界,推演至鸭绿江。且其配合明朝,在经济、军事方面打压女真,导致建州等部女真人,为求生存,亦向朝鲜送质子,谋求官职,祈请贸易。在天顺三年,明朝谕令朝鲜不许接纳女真人朝贡后,朝鲜开始多次越过鸭绿江、图们江征伐女真人,故朝鲜王朝一时成为明代女真社会发展之障碍,此乃明后期女真人仇视朝鲜之根本原因。位于女真西部的蒙古,在兀良哈三卫臣服明朝时,东北蒙古各部多以游牧东渐。正统年间,瓦剌东进后,统括蒙古草原,势力延及女真地区,其后脱脱不花汗东进,基本打乱明朝对女真人实行的羁縻卫所统治,女真头领或投降蒙古,或被杀戮。其后虽然明朝设法恢复了对女真地区的统治,但蒙古各部首领东进,抢掠辽东汉人及女真的活动,不时发生。故有明一代,女真人受制并游离于三者之间,且导致女真各部族之间利益纷争、战乱频繁、弱肉强食,但因之亦造就了明代女真人自立谋生、吃苦耐劳、英勇善战之性格,为其兴起并在改称“满洲”后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以往研究明代女真的成果,基本侧重研究女真人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和犯边抗明等问题,忽略了女真人与朝鲜、蒙古的关系,故难以把握明代女真人整体发展脉络,此亦可为本书之创新之处。
与以往研究著述不同,该书把明末女真的统一和发展列入明代女真史的研究范畴。以往的研究成果,均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历史,列入清朝开国史或清代满族兴起史之中,该书将其作为明代女真人历史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而完备了有明一代的女真史,则从侧面明确了明朝中央政权与地方民族政权的正统与闰位的定位。
朝鲜史料与满文史料
《朝鲜王朝实录》是记载明代女真历史所依重的基础史料,因国内一直难以系统查阅,造成了诸多利用不便。国内学者普遍习用的《明实录》,亦因卷帙浩繁,女真内容零散纷杂,搜罗齐备有一定难度。史料的限制,使得国内学界对明代女真的研究相对薄弱。日本学者河内良弘撰写《明代女真史研究》,曾对《朝鲜王朝实录》中明代女真史料进行了辑佚与整理。赵令志先生在翻译该著作的过程中,收集了《朝鲜王朝实录》中大量有关明代女真的资料,并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行了翔实的考证与补充,将《朝鲜王朝实录》与《明实录》仔细对勘,突破了零散、细碎的史料局限,整体性地呈现了明代女真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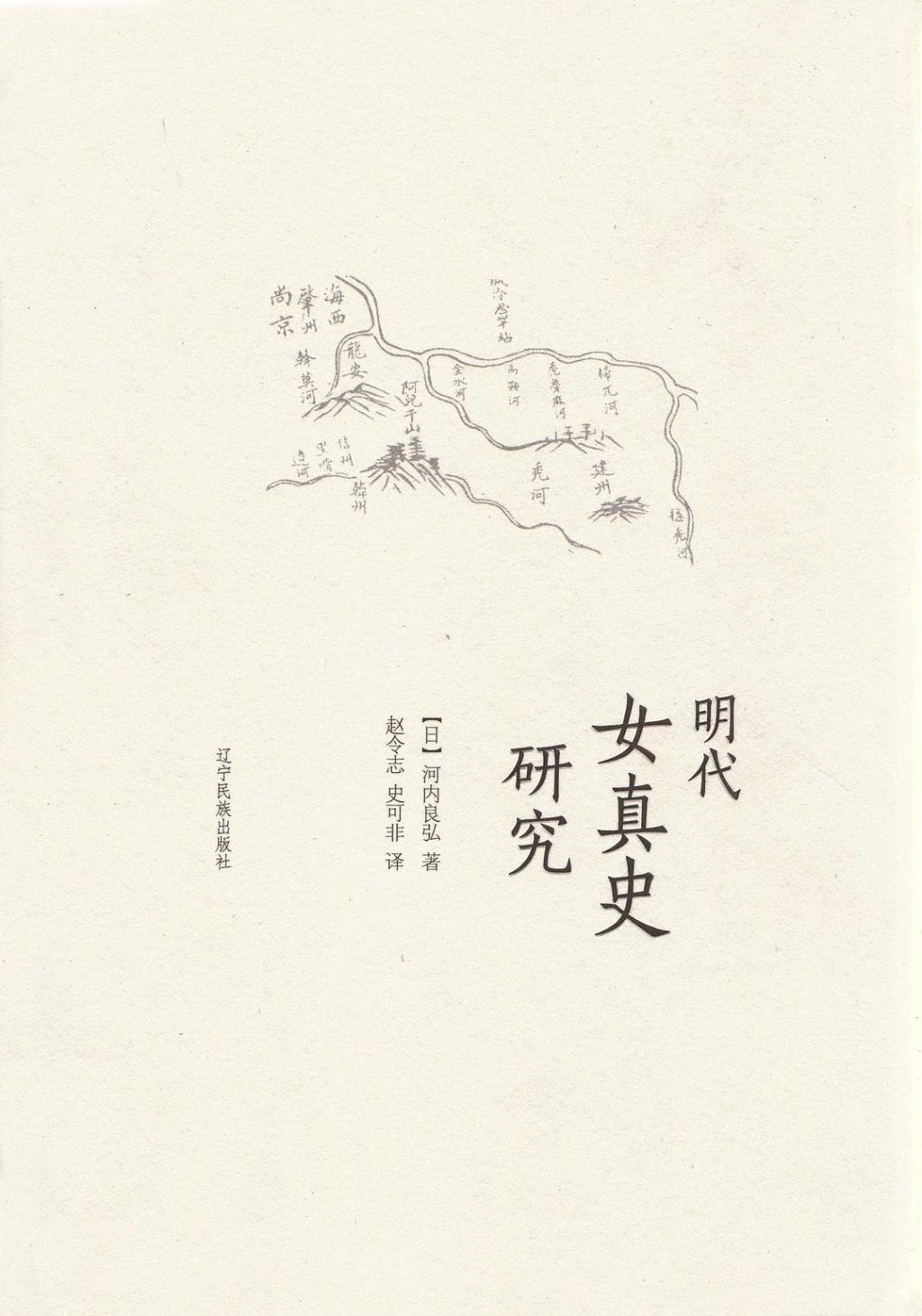
河内良弘著、赵令志等译的《明代女真史研究》
该书对女真——满洲姓氏的研究值得关注,作者利用传统史学爬梳史料的“笨”办法,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为中心,结合《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辑要》《清朝通志·附载满洲八旗姓》等史籍,就其源流、部属及世居地进行了逐一梳理、归类,认定满洲姓氏有六百七十八个,该论证对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将会产生实质性的推进。
重视和使用满文文献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者通过对《满文老档》太祖朝所载明末海西女真的三百六十四道敕书的细致分析,梳理出所属海西羁縻卫所的分布及其在明中后期女真所谓敕书的袭替情况,指出海西女真卫所敕书一直被明朝兵部武选司掌控,到明朝末年海西女真仍分布较广,故不能将海西女真等同于扈伦四部,从而纠正了《满族简史》等著作中海西女真即扈伦四部的观点。根据这批敕书,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明朝嘉靖中对女真卫所朝贡贸易政策之变化,即明朝分别确定海西女真以一千道敕书从开原入贡贸易、建州女真以五百道敕书从抚顺入贡贸易,每道敕书每年以一人一马入边,改变了以往凭着一道敕书可以多人一起入边的政策。同时规定距离明朝较远的女真人,可以“朝贡不常”,不限时日,这部分女真人被明朝列为“野人女真”,自此,明朝方将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分。《明仁宗实录》之前的各朝实录中常出现的“野人女直”“女直野人”的称呼,从蔑称变为专属名称,嘉靖中叶以后则以“女直夷人”取代。且明朝官书中并没有“东海女真”的称呼,“东海女真”最早见于《满文老档》,其中将呼儿哈、瓦尔喀、窝集称为“东海三部”,三部之人称为“东海女真”,从而厘清了何谓“野人女真”的疑案,并指出野人女真的范围和所属,不能将东海女真等同于野人女真。这一创新观点对研究明代女真史和满族史将产生重要影响。
汗号、国号、年号
借助满文文献,该书对学界存在争议的汗号、国号、年号等问题进行梳理和释疑,认为努尔哈齐的汗号abka geren gurun be ujikini seme sindaha genggiyen han 的译文很多,译作“天任抚育列国之英明汗”是最准确的,即上天委任抚育各国之英明汗。许多学者将此翻译为“承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等,而认为汗号中含有“天命”年号的性质,不够准确。abkai fulingga(天命)与abka……sindaha(天委任)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但此汗号已具有蒙古语“合罕”的含义,故此次称汗,具有北方游牧或渔猎民族称汗建国的性质。
关于天命、天聪作为年号问题,蔡美彪先生早有疑问之论,但未得到学界认可。本书根据《满文原档》的记载,认为努尔哈齐时期并没有“年号”,而是以干支纪年和岁次纪年。在后修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里,对此次进表称汗的记载中,附加“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看似天命年号在称汗建国时已使用。但在当时的文献中,并未见到该年号,而在《满文原档》中纪年仍用干支纪年,《实录》里从天命二年始用“天命太祖英明汗第二年”,满文为abkai fulinggai taidzu genggiyen han i jai aniya,可以推测,天命年号应该是皇太极时期编修《太祖太后实录》时才确定的。从满文档案来看,努尔哈齐时期纪年方式是干支纪年,故“天命”并非当时的年号。如“天命”一样,“天聪”亦并非年号,乃天聪汗第X年之纪年方式在汉文中的简写,满文为sure han之第X年。sure han乃皇太极之汗号,为“聪睿汗”之意,其中并无“天聪”之“天”(abkai)的含义,因而满文原意与汉文是对不上的。年号“崇德”,满文为wesihun erdemungge,字意与汉文相同,乃入关前之真正年号,亦为针对“崇祯”年号之产物,乃因皇太极将自己之“崇敬道德”,比之“崇敬祯祥”更高一层之故。皇太极称帝后才有年号,或许更能阐释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设定年号以来,帝有年号、汗无年号的年号使用特征。
至于aisin gurun国号之aisin,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之前已使用,如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出现sure kundulen han amba gurun be isabufi, aisin doro be jafafi banjire 之语,汉文译作“聪睿恭敬汗集成大业,执金国之政”(《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一函,满文见第一册,78页;汉文见第十九册,第6页),此处aisin doro或可译作“金政”,但可知在此时已用aisin为政权名称,此大概与建州女真一直认为“大金乃我远祖”“幹(斡)朵里乃大金之裔”的认同有关。努尔哈齐曾多次表露此观点,如天命四年三月对朝鲜称,julge meni aisin dai ding han de(昔我金大定帝时),天命六年三月对汉人称julge meni aisin han(昔我金帝)、julge suweni nikan i joo hoidzung joo kindzungjuwe han inu meni aisin han de jafabufi(昔尔汉人之赵徽宗、赵钦宗二皇帝,亦为我金汗所俘)等,均可反映出努尔哈齐对金朝作为其先祖的认同,因而在建州女真人中多仍沿用“金”作为国号,此问题日本学者神田信夫、河内良弘均有专论。1616年努尔哈齐建国称汗后,将aisin定为国号。国外学者一般称之为“爱新国”,乃女真语直译。但在当时汉文的史料,将其称作“金”或“后金”。还有学者认为称“金”尚可,称“后金”欠妥,其实在《满文原档》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出现了amaga aisin gurun i han solho han de bithe unggirengge(后金国汗致书朝鲜国王)的用法,虽然较少,但仍可知道满文是有amaga aisin gurun(后金国)一词的。但如此书写,仅见此国书,无普遍性,故应以aisin gurun为准。另从当时该政权的印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即“天命爱新国汗之印”来看,aisin gurun应该最为准确。至于“大清”国号之语义,如“大元”(daiyuwan gurun)、“大明” (daiming gurun)等国号一样,来源于汉语。满文之daicing,乃汉语“大清”之拼写。按古代国号必有所典之制,“大清”一词,或典出《管子》卷十三《心术篇》中的“镜大清者,视乎大明”,以及《管子》卷十六《内业篇》中的“鉴于大清,视于大明”,乃针对“大明”之国号。近来有学者认为来源于蒙古语“daičing”(英勇之意),音虽相近,然与历代定国号之史实不符。且如前引,天聪九年十二月皇太极告祭其父表文所言,“蒙古诸国尽归一统,惟有明国尚为我敌”,因而商定国号,要针对敌国明朝。另按五行之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明以火旺,清以水兴,水可灭火,乃清将灭明之寓意。当时在金国有大量儒臣,汉文化影响较大,且努尔哈齐既通五行,并影响其子侄,皇太极在各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因而,此说应该更符合“大清”国号之本意。
以上利用满文文献进行考订,解决了学界长期以来的争议。对“天命”“天聪”作为年号释疑,只能让学界明确其来历,不可能废止不用。而对国号的考订,可以纠正将“金国”写作“大金”“后金”等错误用法。
八旗成员的多民族性
该书所贯穿的一个重要历史线索,是明末女真人的民族融合与八旗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特征。作者认为:明代女真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与明朝、蒙古、朝鲜接触的过程。女真人不断内迁,与汉族交错杂居,双方在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交流融合,不仅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还促进了双方文化的共同发展。其次,女真人的统一加速了民族一体化的进程,努尔哈赤后金政权进入辽沈地区后,将辽东汉人纳入八旗之下,客观上造成了不同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局面。同时,部分明朝中叶被迁入中原和华南地区的女真人,则完全融入当地汉人群体之中,体现出民族交流交融的地域性特征。再次,建州、海西即部分野人女真人的统一与融合,对满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八旗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满族。明末清初,以女真人为核心,融合了东北其他渔猎、游牧族群以及汉、蒙古等多元文化因素,形成了八旗共同体。八旗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就是融合辽东汉人,迁移而来的蒙古人、索伦人、高丽人的过程。这一共同体在历经清王朝近三百年的治理后,逐步呈现出多元交融的文化特征,最终发展成为满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
女真人的融合历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女真人的融入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包容并蓄、和谐共生的优良传统。作者通过对明代女真发展与演变的探讨,归纳出八旗成分的多民族性:八旗并非由单一民族组成,而是突破民族界限,由多种民族共同凝聚而成的共同体。同时,八旗中的民族成员也并非该民族的全部人口,而是由多个民族的部分人群编组而成,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政治目标明确的社会群体。八旗成分的多民族性,有力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融合,对清朝实现大一统格局并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与国家实践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也成为清代开拓疆域、推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因素。
该书的作者赵令志教授,曾师从著名清史研究泰斗王锺翰先生,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期间,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满族史”课程近三十年。在写作过程中,他尝试“将多年讲授、研究满族史之心得,融入此书设计体例、撰写方法、斟酌体例等方面中”,并吸收其弟子李小雪的研究成果。与研究专题论著有所不同,作为一部断代民族史,该书主要以时代、地域、族群、语言、文化等历史要素为框架阐述史实。诸多富有启发性的创见与精当的史料考辨,并未直接体现在篇章标题之中,而是融汇在简洁平实的行文里,化繁为简,寓论于述,别具匠心。这本大著的出版,不仅深化了学界对明代女真史的具体认识,也将对满族史的整体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