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尔夫夫妇
今年8月18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用了二十多页的篇幅介绍二十世纪重要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这个译名我从前喜欢写成“伍尔芙”或“吴尔芙”,幻想着用花花草草编织出心目中女作家清丽的桂冠,却忘了那原是她结婚后改用的夫姓,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头顶同样的花冠肯定不伦不类,翻译从来不是浪漫的工作,怪我多事了。
杂志上刊载的三篇长文分别谈伍尔夫的生平经历、出版事业和文学魅力。我最感兴趣的那篇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起做书》:从一台小型手动印刷机开始,伍尔夫夫妇创办、经营了二十多年的霍加斯出版社简直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国,伍尔夫本人关于出版的理念、选题和审美,更是这座理想国得以建立的基石,两者命运息息。写这篇文章的顾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科班出身,2023年7月松荫办“纸月亮”展览时他和陆公子一起来过画廊,清隽里带几分腼腆,一派读书读多了才会有的模样。
顾真去年送我的那本《书会说话》是他用中文写的关于英文书籍的书话小品,谈出书,谈贩书,谈访书,谈藏书。印象里中文作家能写英语文学的不少,写过英文书籍的不多。向陆公子请教,他写出来的名单倒也不短:周作人、梁遇春、郁达夫、叶灵凤、冯亦代、董鼎山、杜渐、吕大年、恺蒂、刘铮,不过这些名字顾真在他的书里都没提到,他只说:“董桥先生的书,当年翻得最勤快的大概是《绝色》。搜书藏书旧事看太多,难免青山入梦,恍惚间觉得那些竹节书脊同自己也就相隔一面橱窗。一不小心就成了奥古斯丁·比勒尔(Augustine Birrell)笔下那些初入迷途的年轻猎书客,患得患失,‘叹息余生也晚’(bemoan his you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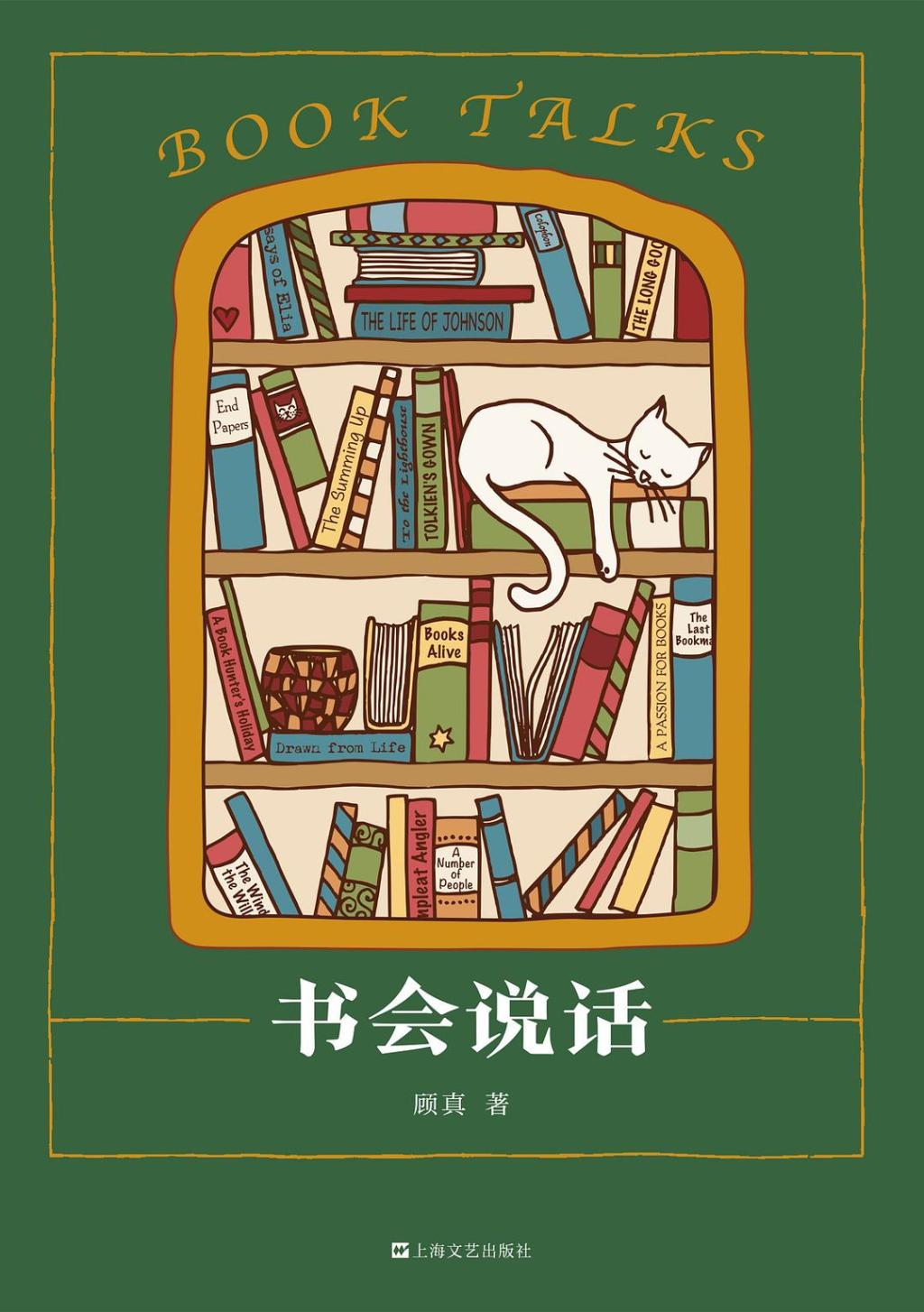
顾真著《书会说话》
生得晚,也有生得晚的好处。1997年陈子善先生编过一本《你一定要看董桥》,用柳苏先生1989年登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出几十篇当时文人读董桥后写的评论,有人爱得深沉,有人爱不起来,是那一代人读董桥后的体会了。1997年顾真才九岁,另一位自称“最早应该是上了香港一位董先生的当:中学时的特长是熟读各种董桥文集,一直认定这世上写英文是没有人写得过毛姆的”。陈以侃才十二岁。早生二三十年他们读了董桥写一点感想或许也会收入《你一定要看董桥》那本书里,只是《书会说话》这样有趣的小书作者就不再是顾真了,毛姆的短篇小说集也可能从此少了一个传神的中文译本。他们这一代人读董桥,已经读得“身体力行”了。
我读董先生的文章不算很早也不算太晚,体会默默不语,体行碌碌无为。这十多年来忝列门墙,谋生的技巧没学几样,花钱的本领很有长进。先是古董清玩,再是名家字画,最后迷上手工装帧的西洋老书,看得上买得起的一本一本都抱回家。早年董先生在牛津出版的那些散文集的设计其实很受他收藏的手工装帧洋书影响,这次松荫替他重印《今朝风日好》要的也是同样干净利落的典雅雍容。做书真难,封面设计,纸张选择,开本和字体的大小,字距和行距的排布,都要尝试,都要取舍。更难的是校对,一本书错漏百出就算做得再漂亮也对不起作者,更对不起读者。错字、漏字多看几遍找出来不算太难,有些读不懂的地方一定要找到原文出处才敢敲定。《楠木好看》引用明代屠隆《考槃馀事》里罗列的四十五种文房器物,有一种“诗筒葵笺”,我最初怀疑是“诗筒”和“葵笺”之间漏了顿号,查了《考槃馀事》原文才知道那是“採带露蜀葵研汁,用布揩抹竹纸上,伺少干,以石压之,可为吟笺。以贮竹筒,与骚人往来赓唱”的雅物。2016年日本电视剧《校对女郎》里石原里美饰演的女主角河野悦子为了保证文章内容准确,会根据作者文中描绘的场景实地探访以确认所言虚实。当时觉得多此一举,编完这本《今朝风日好》我倒真想去托斯卡纳的古城圣吉米亚诺,找一找董先生喝过下午茶的露天茶座,看看是不是能瞭望到满山满谷的橄榄树了。
圣吉米亚诺是San Gimignano,书里面没有译成中文,双语并用,校对又多一分难度。只能怪董先生英文的渊博不输他中文的典丽,《刘文指要》里他说:“李欧梵的洒脱和刘绍铭的沉潜毕竟渗出一些留美岁月浸回来的超逸,一个走过那么debonair的春雨,一个熬尽那么stoical的冬夜。”做了几十年的编辑,写了几千篇的文章,董先生不会不知道中文写作夹杂英语修辞是大忌,这一句写成“一个走过那么明媚的春雨,一个熬尽那么坚忍的冬夜”不难看,更不难懂。可惜真要是那么改了,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如经巴黎春雨滋润的李欧梵翩翩走来,也看不到如受雅典原教禁锢的刘绍铭踽踽独行了。这样传神的双语笔法书里不多,也不能太多。更多的是英语的引文,《最后,迷的是装帧》结尾那段董先生引用的英语松荫照抄牛津初版:“…but by-and-by he takes home books in beautiful bindings and of early date, but printed in extinct language she cannot read.”有好心的读者找出罗伯特·米尔恩·威廉姆森(Robert Milne Williamson)《老书店拾芥》(Bits from an Old Bookshop)里的原文,告诉松荫“she”应该是“he”。当然!“he takes home”的书“she cannot read”是常理,有什么好强调的?真要感谢这样的读者,《今朝风日好》再印那天,这样的纰漏一定会改。
顾真在《书会说话》里说:“伍尔夫夫妇做出版很有一套自己的思路,选题力求新颖,宣传不事张扬,尤其在书怎样才算‘漂亮’(look nice)这一问题上,很少让步。哪怕一时不为大众接受,乃至被书店拒之门外,依然能坚持独到的品味和审美。”松荫没有在出版业上高歌猛进的野心,有幸能编印的都是董先生的旧作,选题自然无法新颖;势单力薄,宣传当然也做不到张扬;唯有在“漂亮”这件事上,松荫才可能向霍加斯出版社看齐,装帧要做得漂亮,内文更要做得漂亮,不能让步,也不会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