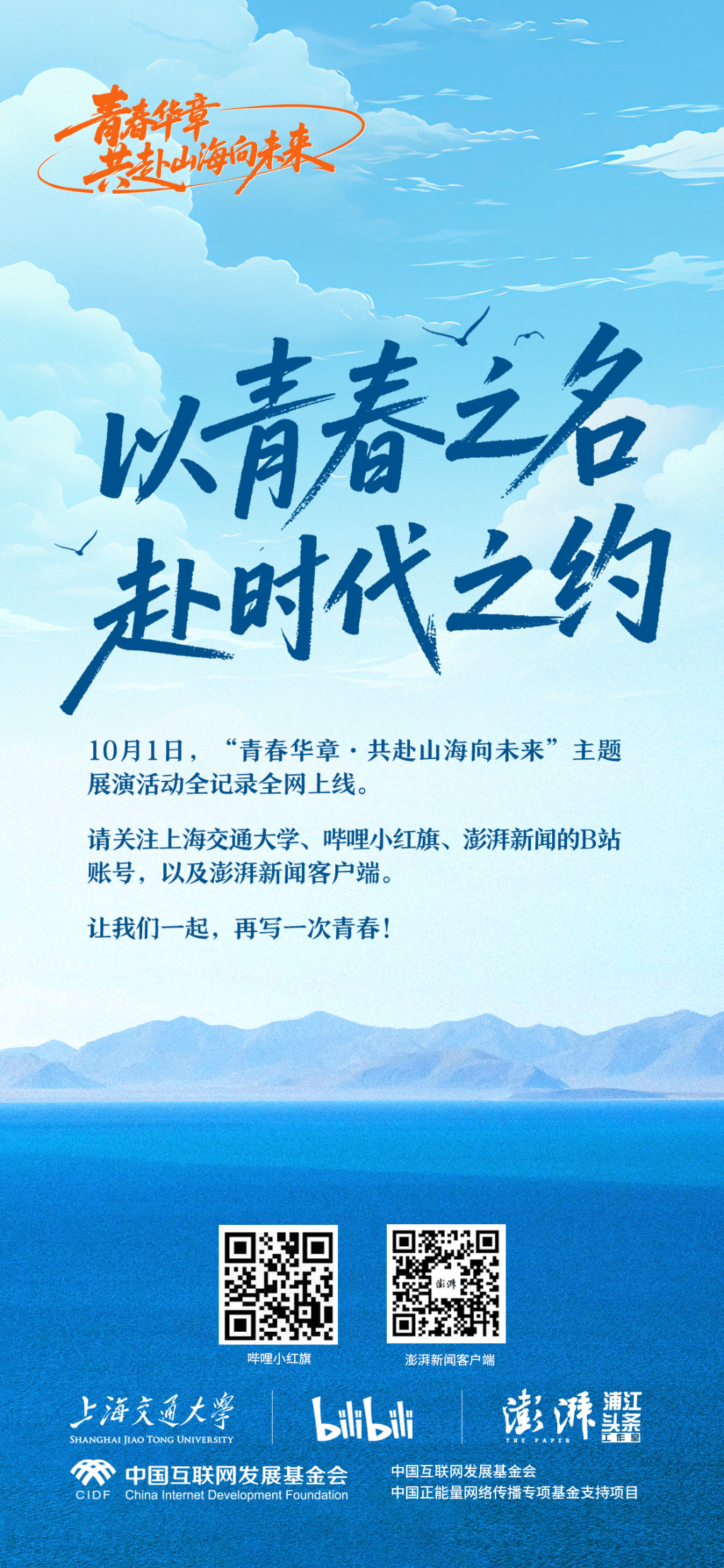摘要:作为当代自嘲文化的代表," 牛马 " 一词背后同样存在一种共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比起让别人来打我,自己先下手更有分寸 ",面对劳动过程缺乏话语权和尊严的职场窘境," 牛马 " 们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驴 " 的概念是相对于 " 牛马 " 一词的外来者,自嘲者们不仅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还要同样先下手为强地将外来者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推荐安歌同学的深度好文,不要温和地走入那道缝隙。
吐槽青年出品陈安歌|文
近日,中国畜牧业协会驴业分会相关负责人向中国 · 新闻周刊确认了我国缺驴一事:" 目前我国牛马都不缺,就缺驴。" 以 " 牛马有的是,驴不够了 " 为标题未必是有心之举,但一定是时势使然:畜牧业行情与职场状况微妙重合,上班族与草食者惺惺相惜,一行文字打通两个领域,竟能引发无数 " 牛马驴不相及 " 的隐喻讨论,确然是一场语言的奇观。
" 牛马 " 其实不是新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开头即自称 " 太史公牛马走 ",后世一众文人纷纷提笔,写 " 自憎牛马走 "" 公怜牛马走 ",言下之意乃是任人驱驰,辗转无定,与当今的职场用语颇为相近。然而细究起来仍有区别:从 " 牛马一样的仆役 "、" 像牛马一样地奔走 " 到 " 牛马 ",人的身份和行为主体被隐去;从礼仪性、文学性用语到日常化自称,偶尔抒发的怨怼之情变得普遍化娱乐化。从 " 牛马走 " 到 " 牛马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越来越物化,姿态越来越低,哀痛感越来越弱,于是自谦演化成自嘲,自嘲发展成自黑,最后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终于有一天另一个人偶然经过了牛马们的话语领域,整片黑夜突然沸腾起来——所以不要温和地走入那个良夜。
作为当代自嘲文化的代表," 牛马 " 一词背后同样存在一种共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比起让别人来打我,自己先下手更有分寸 ",面对着个人价值得不到实现,职业生活不符合预期,劳动过程缺乏话语权和尊严的职场窘境," 牛马 " 们选择了先下手为强,承认自己身处窘境,抢占仅存在于互联网平台的话语高地,从而达到心理层面上脱窘的效果。自嘲的另一面是反讽," 牛马 " 也可以是一个收放自如的词语,因其贬低性内化为职场环境的自适应,因其庸俗性外放为对工作体制的不满情绪,以单薄的话语权营造出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牛马幻境,成为职场打工人的防御机制。
个体的防御会成为集体的空间,而社会认同把个体聚集成集体。在生产过程中个体所创造的价值被流水线式的工业模式消解,在劳动关系中个体的自主性被言听计从的职场文化消解,在社会待遇中个体的满足机制被日渐严苛的工作待遇消解,从以职业属性定义的 " 都市白领 " 到以劳动属性定义的 " 早安打工人 " 再到如今以生存境遇定义的 " 牛马 ",范围扩大,地位下降,情感贬义化,实际生活中年轻人面临的是普遍失权境遇下越来越不稳定的身份属性,而随着经济周期下行,不稳定的身份属性动摇了社会认同。
我们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牛马 " 之类自嘲话语的兴起,实质是我们无法在追求意义的主流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只能倒向意义的反面,即通过不断地宣扬自己身份的缺点来吸引共同的身份群体,渴望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语言和意义之间存在缝隙,领域和领域之间存在缝隙,解构传统意义成为另一种意义," 牛马 " 一词便游走在传统畜牧与职场属性之间,年轻人在缝隙中寻找容身之所,在话语环境中开拓立足之地,在一次次的自嘲中搁置人生的意义,迎来话语层面的 " 狂欢 "。
躲进用自嘲开拓的话语缝隙,已经成为上班族的一种防御姿态。这个缝隙中的全体居民既然对彼此怀抱着获得认同的希望,就必然对外来者保持十二分的敏感。因此 " 牛马驴 " 之标题一出,大家迅速对号入座,拿稳身份牌,试图通过隐喻方式捍卫自己对牛马一词的话语权。而语言的神奇之处还在于此——自嘲者们突然意识到 " 牛马 " 一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景:垂直层面上," 牛马 " 之外还有长期被忽视的 " 牧牛马者 ";水平层面上,吃苦耐劳的 " 牛马 " 之外还有身负 " 犟 "" 繁殖能力强 " 等标签的 " 驴 "。好,不管合适与否,拿来吧你!畜牧业负责人是相对于发言群体的外来者," 驴 " 的概念是相对于 " 牛马 " 一词的外来者,自嘲者们不仅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还要同样先下手为强地将外来者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
当 " 牛马 " 一词的传播量足以发展起一场话语狂欢时,人们便 " 转守为攻 ",不只满足于通过排除不理解自己反讽的群体来保障话语权利,而希望拓宽 " 缝隙 ",让更多人接受自己的话语体系。" 在毫不相干的领域进行发言 " 这一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渴望被看见,渴望拓展缝隙中的生存空间,呼唤更多境遇相同的人一起抱团取暖——话语中的缝隙是动态的,生长与消解并存,解构与重构同时进行的状态。因此 " 牛马驴 " 一事看上去是畜牧从业者误入年轻人的话语缝隙,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却是自嘲者对社会热点新闻展开解构式攻击,试图消解掉文章的本来意义,在本来毫无歧义的文本中找到可供栖身的新的缝隙。
缝隙存在于语言与引申义之间,存在于吃草的牛马与上班的 " 牛马 " 之间,存在于发声的网络与失权的现实之间,成为自嘲文化生长的土壤。只是,当我们观察缝隙时,还应该看看缝隙之外的地方:夹缝生存难道已经是生活的常态了吗?